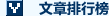延安回忆录
阿甲遗稿 王永敬 符丐军 符挺军整理
阿甲,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1907年生于江苏武进,著名戏曲导演、理论家。自幼随父读书,习书画,生性聪颖,在当地有“十灵童”之称。1938年春,他奔赴延安,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始用艺名“阿甲”。毕业后,任该院平剧(京剧)研究团团长,专门从事戏曲的编导及理论研究工作,探索京剧的改革实践。1942年,任延安平剧研究院院务委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院长。延安时期,他参加了著名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的改编和演出,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处副处长、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室主任等职,并参与编导了现代戏《白毛女》《柯山红日》《红灯记》等。20世纪80年代起,历任中国京剧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及戏曲理论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晚年定居无锡,任江南书画院名誉院长。1994年12月24日病逝于无锡。
本文根据阿甲先生1989年4月的手稿整理而成。
一、向往延安
从1937年家乡沦陷后,我便一路沿着长江徒步走到湖口,乘轮船到武汉。那时一心向往延安,没有找到门路,便先进了国民党的“技术训练班”。进去后,里面大都是一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并无什么技术可学,只是讲讲抗日宣传,后来又改为“湖北乡干训练班”。此时,我得悉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就自动脱离“湖北乡干训练班”,进了山西“民大”,地址在山西运城,是山西临汾总校的三分校。进校后,我感到民主空气浓厚,可以公开看到延安的书。那些教员讲唯物辩证法哲学,同学们公开讨论政治形势,进步的倾向性非常鲜明。我记得有一次激烈地闹起反对张慕陶“托派”的运动。那时我虽然认为阎锡山开明,但感到对革命总不如共产党彻底,所以目的还是要去延安。当时传延安和山西有一种说法,延安“抗大”不收山西“民大”的学生,我不甚相信。“民大”生活还可以,发了军衣,吃到馍馍,菜蔬尚可。有一个夜晚,全校师生数百人,在大礼堂,点着汽灯,席地而坐,讨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社会科学的定义问题。当时大家即兴发言,大都空洞无物,言不及义。话头转到保卫山西的国土上去,一些教师慷慨陈词,一些名人发言“要把最后一滴血流在山西”。可一到第二天早晨,昨晚发言“誓死保卫山西”的那些教师和主持会议的名人,忽然影踪不见,说是都溜走了。学生哗然,知道时局紧张,都要求在山西风凌渡去陕西。记得是学校的教务主任梁化之,领着学生去风凌渡观察,一看一只船也没有。实际上是校方不肯放学生过河,事先将船封锁。学生只能回到原校,梁化之便派领队将学生编几个中队直接进发。学生们手中无枪,只给发了几个馍馍、几块银洋。一路之上,街道乡村已经撇家闭户、没有人烟。有一部分学生看看去向不明,不知何处着落,就要求脱离部队自找出路。我也赞同,便去寻黄河渡口,跑到一个叫“小船坞”(地名就记不清了)的渡口,一到渡口,看到卫立煌等几个军官,带着军用器材,渡过黄河。我们这些学生和“患者接送队”交涉,借抬伤兵之名,抢渡黄河。我不慎落水,幸吊住撑船竹竿,爬上船帮,未曾淹死。渡过黄河,就到了陕西的地区韩城,在那里休息下来。之后山西“民大”学生陆续渡河,到了韩城。我的同乡徐特、蒋干城也过来了,患难相聚,大家都很高兴。那个时候,听说临汾已经陷落,运城也很危险,山西看样防守不住了,学校也缺少撤退计划,所以秩序很乱。我们到了韩城,山西当局不愿我们散落各地,又重新登记“民大”学生,每人各领五块银洋,暂作伙食之用,说是“民大”要在韩城重新成立。学生中有冒名顶替领过几次钱的,我只领了一份,实际上作为赴延安之用。没有几天大部分“民大”学生都离开了韩城到了西安,再到办事处登记,去到延安。至此,我向往延安的愿望总算实现。
我记得那是1938年春节前后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和徐特在山谷下的大道散步,天已黑,仿佛看到两旁矗立着高楼大厦,在黑沉沉的窗孔里,透出微弱的灯光。一夜过来,才看出是连绵的山头,从山腰到山脚,分层次地削平了山面,又分层次地挖掘出一排排的窑洞,那个微弱的灯火便是阅读马列主义的麻油灯盏从山洞的窗口里透出来的。每天早晨,满山遍野都是歌声,唱的是抗日歌曲和《延安颂》。这时候各学校新来的学生,可以不领饭票在各校吃饭,陌生人见面都亲切热情。我在抗战流亡生活中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民主气氛,真是看到了自由王国。延安有“抗大”“陕北公学”“鲁迅文艺研究院”。我是来学军事政治的,当然进“抗大”合适。同来延安的一些“民大”同学知道我会画画(因为我在“民大”画过抗日宣传画),劝我进“鲁艺”。我考虑“鲁艺”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当然教的是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是分不开的,自己又是爱好艺术的,如果能和政治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为共产党工作的人,为抗战服务,为自己的艺术前途着想,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因此就决定去考“鲁艺”美术系。
“鲁艺”有四个系:文学、美术、音乐、话剧,院长是沙可夫。美术系的主任是沃渣。考取了美术系后,我们就在山洞里住下来。学院的伙食很简单,吃饭是分组聚食,蹲着吃。仅仅一盆蔬菜,又很稀少,吃的黄米饭。每逢吃面条的时候,以木桶装,放在地上,同学们弯腰捞面,叉子、筷子混搅在一起,手脚碰来碰去,面桶里还曾捞出钢笔。这并不是窘态百出,而是青年人一到革命的自由天地,变得天真活泼,不主张训雅文质彬彬之风。因为居住困难,有的地方要开山挖洞,安置住室,同学们都以这种改造自然的劳动为荣。
我住下来后,写过简历,毫无顾虑地把国民党的身份也交待了。一是我真心诚意地要投奔共产党,认为只有在抗日统战中共合作时期才能有机缘如愿以偿。我所以向往共产党,是看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国民党腐败无能,使人失去信心。二是我在加入国民党之后,读过一点进步的书籍,最初是读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又读了李达翻译的《唯物辩证法》等。
我进的是美术系的第一期,记得起来的同学有秦其谷、华君武、陈叔亮、钟惦棐、谷牧等人,有的想不起来了。和我一起到延安的徐特同志,初来时进“抗大”,后来也转到“鲁艺”美术系。那个时候,我们画抗战的宣传画,也画速写和素描。我过去是画中国画的,没有素描底子,所以大都是以国画的笔法,讲究笔法线条,不重形体解剖的准确。我记得在“鲁艺”画了一些水墨人物画,经过战争,路途迁徙,当时延安的笔记还有一本,图画则一张也没有了。1987年某一天,一个叫姚淑平的老干部,是名女同志,拿出一张水墨肖像给我看。我一看确实是我的手笔,肖像人物的姓名不记得了,姚淑平说那是她丈夫的画像,她丈夫叫梁金声,是在延安新市场当大夫的,后来由中央派到安南(越南)工作,再后来牺牲了。姚淑平携此像在身数十年。她说这张画像比他的任何照片都更有神态,所以保留至今。可惜画像一角,我的名字已经撕毁,此番找我,就是要我重新题个名字、盖章,并跋了辞。姚淑平珍惜这张画像,是珍惜他们的深厚感情,我也把它复印一张,作为延安时代美术作品的纪念。
二、从一支歌曲唱起
考进“鲁艺”后,在一个晚上,记不得是参加一个什么机关组织的文艺晚会上,礼堂很大,很隆重。大家唱抗日的流行歌曲,轮到我,我说我只会唱京戏,大家听了反应冷淡,但等我唱完之后,掌声非常热烈。因为我是将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之歌》,用京戏中“西皮流水”板的形式唱。虽然一字未改,但是抗日游击队的心理动作,那种既秘密隐蔽又突然伏击的行动,这种音乐形象通过京戏“流水”的旋律和节奏的样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唱出了另一种音乐形象的《游击队之歌》。这对于我来说,也并非随口唱出,而是在抗战歌曲的气氛中经过心里琢磨、嘴里哼哼出来的,又因为是在晚会上的一种即兴表演,所以这也算是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的一种尝试。想不到这种“逢场作戏”在客观上安排了我的命运。之后,我又和陶德康排演了《夜袭飞机场》,和江青排演过《松花江上》,和任桂林排演过《钱守常》。那时还是半业余性质的,是各个单位调演的。那时,这些新的演出都很受欢迎。组织上把我从美术系调到鲁艺实验话剧团工作,在剧团里筹划京剧组,要我把京剧作为终身事业来做。我深感疑虑:感觉自己抛妻别子来延安是为了学政治、学军事、学共产党的革命道理,不是学京戏来的,叫我搞美术犹可,搞京戏,似乎与共产主义无关。新的革命文艺有“左联”传统,和戏曲没有什么联系,何况“五四”是把戏曲否定了的。我这样想来想去,总觉得不是滋味。但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把戏曲当作抗日统战的对象来看,戏曲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作为对旧形式的一种改造,让戏曲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不也是和政治相关的事业吗?于是我便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京戏(包括所有剧种)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真正的发展前途;另一个是我本人所具备的条件,是否适合做这项工作。后来经过组织的说服,我终于决定以党领导的京剧改革作为自己的事业。于是,鲁艺实验剧团成立了一个京剧小组,剧团负责人是王震之,记得最初是有八个人,有张东川、卜三、王九成、任钧、陶德康、刘佳、徐本和我。这八个人比较固定,后来也有一些人是调来调去的,姓名都不记得了。演出时人员不够,临时从鲁艺旁的系抽调出来帮忙。有一个时期日军的飞机常来延安轰炸,城市的礼堂已被炸毁,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排戏,在山崖岩石的掩蔽下排练,上课时只要听到飞机响声,就钻山洞,山洞里还有通道,所以极为安全。
三、延安的文艺生活
我们京剧演出有一个特点(那时北京叫北平,故称京剧为平剧),即一开始就是为政治服务,因所处的时代是抗日战争的时代,那时的口号叫做“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又叫“旧瓶装新酒”。那时,我们这些当过票友的人,演出的旧戏不多,掌握的程式也极有限,所以编排新戏,确定内容的同时,总是同时想到旧戏套子,情节尽管可以改头换面,而表现情节的结构,往往沿用老套路,例如《松花江》说的是江边的渔民抗霸抗税,渔霸则以日寇为后台,引发一场激烈的斗争。这个戏部分沿用《打渔杀家》的路子改编而成。里面几个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所以当时这是“旧瓶装新酒”最有影响、也是演得最多的一个戏。这个戏是我和江青合演的,参加者有张东川、李伦、成荫、张诒等同志。1938年秋,鲁艺话剧系排了《流寇队长》,音乐系和话剧系排了新歌剧《生产进行曲》,京剧组排了《松花江》。这三个戏轰动一时,开始演的一天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有一种形式使人感到滑稽,人民同抗日英雄人物竟穿上蟒靠,长髯花盔,脚蹬厚底子靴,以抗日将领的名衔自报家门,这是观众所不能接受的。有一次,中央文委的领导潘汉年同志作了一个报告,我记得他提到京剧演抗战题材,要批判地继承传统,不能全盘地搬过来,京戏还要演些爱国主义的历史戏。
1939年秋,鲁艺平(京)剧研究团正式成立,在礼堂开成立大会。我记得有罗合如、陈冲、李伦、陶德康、张梦庚、任钧、方华、陈怀平、秦臻(女同志大部分都是从女大调来的)、浪影、简易才、石畅、展宇、李碧岩、苏远、田金雪、朱明哲、周品云、王铁夫等二三十人,有些人姓名记不起来了。还有一批受培训的,王双来、张福兴、许万恒、侯铁山、张树全、姜万福等人,其他名字也忘记了。这些人一面学戏,一面“跑龙套”。组织上派我当团长,罗合如当副团长,陶德康当教练,我还是演戏为主,行政日常工作由罗合如同志担任。
由于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首长多、干部多、学生多,都很喜爱京戏。这样,那种穿时装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现代戏就改成间接为政治服务。比如《群英会》,孙刘搞统战联盟去打曹操,其中,在联盟中发生严重摩擦的矛盾;爱国主义的戏如《八大锤》;阶级斗争的戏如《打渔杀家》;向统治阶级造反的戏如《宋江》;仗义执言反抗官僚制度的戏如《四进士》等。其它戏,有些反动或有庸俗低级趣味的,要么不演,要么加以改造。在杨家岭大礼堂演戏,观众大部分是中央首长,对内容的选择比较宽松。这个时期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戏(指京戏,不是所有的戏)逐渐就转为以丰富延安的文娱生活为任务。延安提倡京戏这个问题,鲁艺个别同学也有反对的,在墙报上引起过争论。李伦同志写过反对的文章,较有说服力。反对京戏的同志无非是用“五四”的观点,而同学中抱继承传统的观点的多,所以争论也就平息了。后来发展到各个学校机关,每逢动员生产、庆丰收、开纪念庆祝会、欢送干部、上前方和欢迎归来、杨家岭接待外宾、招待干部等等,大都要求看京戏。先是邀请的机关供给两餐,大都是以脸盆装肉,装油炸豆腐,或其它杂烩,鲁艺旁的系有要求去帮忙的,为吃一顿美餐。文学系的王康同志就是经常去帮忙的一个人。后来邀请演戏的单位除供饭外,还要出若干斤粮食。这种做法原来没有规定,是自然形成的。这些事都由剧团里唱花脸的石畅同志去联系接洽。我们到城南的新市场做营业演出,那是延安城市经日寇轰炸后在山湾子里新建的一个商场,商业比较集中,观众中商人和居民较多。因为不是为公家演出,运送衣箱的交通工具就不能那么方便。那时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舞台工作队,一到演出,衣装、道具、汽灯都是演员分箱负载,团长也是一样。居住桥儿沟的鲁艺学院,离城有二十余里,上城去演出要绕过宝塔山,经过飞机场,演完戏再回桥儿沟。
延安的京剧那么流行,并不是说鲁艺京剧团的戏就演得多么好,而是鲁艺京剧团正是要学习技术的时候,借机实践的要求比较强烈。再则是演传统戏所费的时间不多,不像新排一个话剧那样要几个月的时间。延安的话剧也是常演的,如鲁艺实验剧团、戏剧系,就演出过《带枪的人》《马门教授》,戏剧系的《一言堂》《日出》等,新歌剧《白毛女》《周子山》等。《白毛女》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新歌剧创作。音乐创作则有《黄河大合唱》等。青年剧院演出了《雷雨》《上海屋檐下》《抓壮丁》等。鲁艺学校也演出了《吴满有》等。延安还有鲁艺演出创作的秧歌剧,是反映延安生活的。延安的“群众剧团”是陕北的地方戏剧团,极受群众欢迎,《血泪仇》《十二把剪刀》是他们最有影响的剧目,是柯仲平领导的。这些戏在首长、干部、学生中都很受欢迎。
延安的文艺娱乐是广泛的。晚上,用稿纸遮盖着汽灯,乐队演奏着,穿着草鞋跳舞。夏日,在清清的延河游泳,延河的边头是一片沙滩,可以晒着日光睡觉。白天我们在礼堂上课,周扬同志作文艺报告,杨松同志讲马列主义课程。记得鲁艺未曾搬到桥儿沟,我还在城南居住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来鲁艺作关于《红楼梦》的报告,使同志们对这部小说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前线首长返延来作关于在前线打日本的军事战斗的报告,这些报告不但使我们认识了前方战斗生活中的艰苦与战略,也增长了我们的军事知识和必胜的决心。
四、到毛主席家里去
毛主席住在杨家岭,我记得一排有三孔窑洞,窑洞之间是打通的,可以行走。一孔是睡觉的,一孔是办公的,一孔是吃饭和休息的。毛主席习惯彻夜工作,白天睡眠,有时白天起床休息。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正在休息,开留声机听。我听到其中一张片子是言菊朋和新艳秋合唱的《梅龙镇》。他老人家很欣赏这张片子的唱腔,对言菊朋的念白尤感兴趣。他说这张唱片唱得优雅、清静,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节奏既快又嘈杂,听不来这些,到共产主义时代,这些东西会存在下去的。另一次,我演了新编抗日京剧《钱守常》,他表示赞成,并说穿这样的服装不容易舞起来。江青过来对我讲:“毛主席看到你身体瘦弱,要给点钱与你。”我说要钱没有用处,就谢绝了。之后她拿出一瓶药水,说是一种补药,叫“铜碘”,是人家送给主席,主席转送给我的。我收下带了回去,但没有问如何服用。当时正值西红柿丰收,我床下有大堆的西红柿。听说西红柿也是补品,我就一手拿西红柿吃,一手拿“铜碘”喝。吃喝后睡了一觉,觉得鼻孔发痒,原来是鼻孔流血了。可能是补得太过了,也可能是对服用这种补药没有知识。
有一次,我和方华一起去毛主席家里。方华常去杨家岭朱仲丽(王稼祥夫人)家里跳舞,有时也到主席家里去。这一次去,主席正在吃饭,菜很简单,一碗烧萝卜,一盘辣酱,一碟子炒鸡蛋。毛主席邀我们一起吃便饭。我和方华三筷两筷就让碟儿露了底,主席拿筷敲敲小碟的边沿,问道:“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呀?”警卫员站在旁边没有做声,我和方华感到很不好意思,随后就听起戏来。
还有一次,我到杨家岭礼堂演戏,遇见毛主席散步,他随口谈到剧团里的事情,我也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他说:“对同志们政治上要宽些,艺术上要严些。”我当时一愣,没有说话,碰到团里的人也没讲起这事,一直到下山都没提起,怕讲出来人家不信,反倒惹起麻烦,他老人家会讲“政治上要宽些”这句话?我想来想去不解其意,后来想到一种解释,所谓政治上宽些,大概是指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样的解释不晓得对不对。
我在1939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直到1940年秋冬之交的一天晚上,陈云同志来和我谈话,我把我的经历都对他讲了。他对我家乡的情况很熟悉,所问的问题我都能回答上来。这样谈了一个晚上,我的入党问题解决了。由于我参加过国民党,所以要三个入党介绍人才行,我的介绍人是:宋侃夫、黎明、张守维。转正的候补期是三个月。我的入党仪式是在鲁艺平剧团的一间屋子里进行的。我记得满屋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还有俄罗斯著名的作家果戈里、托尔斯泰等人的像,都是我用水墨画画的,就是没有画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等这些京剧的祖师爷。因为他们在革命文艺传统里没有影响,也找不到他们的照片,也无从造像。我宣誓时心里激动、兴奋、自信。我有一种新的感觉。同时,我也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把京剧的改造事业作为我的工作任务,我还没有做好,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因此有些惶恐。
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经常闹摩擦,说要停发边区政府的军费。朱德总司令号召说:“当前我们有两条路,一个是大家散伙,一个是自己种粮开荒。”于是,全体干部、学生都亲自动手,真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我们晚上演戏,白天开荒,这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赢来了丰衣足食,也改变了个别文化人认为参加体力劳动就失去了他的价值的错误观点。
五、成立延安平剧研究院
有一天鲁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说前线贺龙部队的“战斗平剧社”要来延安和鲁艺的平剧研究团合并。消息一来,大家欣喜若狂。贺龙部队有两个宝,一个是球队,队员都是部队里选出来的健将;一个是“战斗平剧社”,成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选出来的有修养的票友,一部分是参军的班社里的职业演员。他们的衣箱齐备,是打仗中得来的胜利品。贺龙同志为了扩大和提高延安的平剧运动,丰富延安的文娱生活,割爱把这个剧团送来。这件事有好多首长关心,由康生安排,将鲁艺的平剧研究团和前线的“战斗平剧社”合并在一起,成立“延安平剧研究院”,由中央办公室主任邓洁同志具体办理。这大概是1942年初的时候。“战斗平剧社”的人数比鲁艺平剧研究团要多得多,技术水平也较整齐。团长是王振武,唱青衣。行当中唱老生的有张一然、齐济民、薛恩厚、齐修林、王炳辉、霍炳林;唱旦角的有小贾、杨呈祥、胡振之;净有刘永汉、赵春华;武生有王洪宝、张一山、刘宪华、刘宪增;丑有赵奎英、袁广和、周品义等;管灯光的有苏远和田井雷。参军的职业艺人能跨演各种行当,他们也有一批学员如小崇、刘起才、林秀芳等。两个剧团合并后,地址搬到大砭沟,占两个山头。研究室在东山头,有李伦、魏晨旭、石畅和我。演员队在西山头,人数较多,窑洞也多。大概成立两个队,我记得队长是袁广和、张梦庚等。
1942年初,我们择日举行了成立“延安平剧院”的典礼。当时还特意出了一本《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刊物,是刘涌汉设计的封面,内有毛主席题的四个大字“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是他老人家第一次在这里提出来的。以后到北京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又加上“百花齐放”四个字。于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联在一起成了文艺上民主、继承、创新的指导方针。这本刊物里还有朱总司令的题词、李鼎铭的题词。由邓洁写了前言,谈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方针任务。大意是谈京剧的统一战线工作问题,京剧为抗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继承遗产和发展的问题。还有一张领导和工作机构表:有院长、院务委员会,有秘书长,有研究室,有演员队等。刊物上有好些同志写了文章,我记得有柯仲平、张庚、李伦、任桂林、魏晨旭、王振武、王铁夫、徐特及我的文章。最初是康生当名誉院长,邓洁当院长。我记得任桂林当过一任院务会议主任,王振武当秘书长,我当研究室主任。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换了好几个,邓洁之后,该院由联防司令部领导,张经武、柯仲平任院长。后来归中央党校领导,由刘芝明、杨绍萱当正、副院长,直到1947年要下山的时候,由罗合如和我当正、副院长。后来就和华北联大合并,那是到华北正定县的事情了。
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合并之后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有了分队演戏的条件,可以下乡、下部队演出。我们演员的条件虽然好了,但是演出的环境还是很艰苦的。寒冬腊月,在广漠荒凉的土台上演出,四面透风,后台的遮蔽极为简陋,既无炭火,也无茶水,我们的演员都无饮场的习惯,只是演戏后卸妆用水。演员出场,看见台前大队战士端坐在地上,台上锣鼓喧天,台下寂静无声,演到精彩之处,阵阵掌声响如霹雳。即使雪花飘飞,战士依然兀坐不动,这种精神非常感动演员,所以演员演戏时无一丝松懈。夏天演出时,虽烈日炎炎,演员汗湿脊背,也不肯有半点偷懒。在农村演出时,老百姓听说是毛主席的剧团来演戏了,就不远数十里赶来看戏,他们平时常看的是陕西当地的地方小戏,所以看到既有曲折的情节又有武打场面的京戏,就感到很热闹、很新鲜。
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在全国都有影响,好些演员想到延安来,因国民党的严密检查而来不成,也有冒险而来成的,如《富连成三十年史》的作者唐伯弢,在北京新兴起的唱老生的李更生,还有演丑角的王炳亭,唱梆子的杨呈祥也都来了。可以说,延安平剧院的主要影响在于戏曲界已知道延安有戏曲运动,大家都抱着一种憧憬和希望,使自己的事业与延安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六、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夏秋之际,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我记得柯庆施来剧院作了报告,要求充分掌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实质。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于个人的责备,而着重于分析错误的原因,目的是要求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我想到一个党员难免犯错,犯错能够不掩饰,在处理方法上,又不是只采取惩罚的办法,而是采取批评教育的办法,这样的党是无往而不胜的。通过学习,大家不仅认识上提高了,道德品质上都提高了。但我没有想到,势头一转,会由康生来搞“抢救运动”,在“抢救失足者”的口号下,以“逼、供、信”的办法,把反特扩大化,幸亏中央及时发现,作了纠正。
这个错误在剧院的开头是这样的:忽然召集我们去听报告,实际上是去听几个自称是来延安做特务的机关青年现身说法,表示悔悟,希望大家也像他们那样交待。开始时,我相信,受震动。之后,这种形式的报告在各机关蔓延开来,文艺团体的鲁艺、青艺、部艺都有这种情况。延安平剧院也有人坦白了,此时我半信半疑。后来,越整越多,那时虽不打人,不抓人,但“逼、供、信”是严重的,鼓励坦白有功。凡坦白过的就随便咬人,这种叫“交待”。领导上很鼓励这种“坦白交待”,所以“特务”越来越多。有一天,八路军大礼堂号召大家坦白交待,当时好些人坦白了,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轮到我时,一个做保卫工作的钱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阿甲,你的事情你自己明白,你是经常往毛主席那里去的”。这话虽很轻,但我的压力很大。心想,我抛妻别子到延安来革命,现在却硬要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不是欺骗党、欺骗自己吗?我不能这样做。于是我上台就说:
“我参加过国民党,但不是特务。”别的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下了台。这位钱处长很不高兴,认为没有起到号召作用,反倒起了破坏作用。自那之后,我就被调到了联防司令部接受审查。
那时,延安平剧研究院为了搞生产,归联防司令部领导,院长是由联防司令部的参谋长张经武兼任的。一个晚上,他们把我调到司令部审查,说我是知识分子,是搞过政治的人(指当过国民党),要我坦白交代,为党立功,还说这是为了挽救我。他们的态度还好,讲的话很有分量,气氛是严肃的。但是我坚持实事求是,任凭怎样也不可能违背良心承认自己是来做特务、搞破坏的。这次的审讯没有结果,于是我就被调到司令部接受长期审查。
那个时候是所谓“抢救”时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时,有的机关还出通讯,报告某机关学校查出百分之几的特务,比例高得惊人,反使人不敢轻信。我心里想,原因恐怕在“逼、供、信”,被逼供的人多了,组织上难以清理,一时不能确定谁是谁非,只好暂时搁在那里。有的要靠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去调查。因此,我写了一封密信给张经武参谋长,我在信中说我的问题明年此时一定会搞清,此信留作凭证。我在联司居住,每天练功,有时有专人和我谈话。后来又把我转到部艺审查,从部艺又转到青艺,隔年后又从青艺调回延安平剧研究院。后来,延安平剧研究院由中央党校领导,院长是党校的教务主任刘芝明同志。自从剧院归中央党校领导,审查的气氛就缓和多了。院内的人可以谈谈话,路上遇到院外的人,也可以点点头,笑一笑。一次,刘芝明院长到院内作报告,我记不得原话,只记得报告精神,大意是说这次审查干部,整错了人是因为“逼、供、信”,所谓“逼、供、信”就是用法诱导你,强迫你非承认不可,你承认了,做审查工作的人就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大家听完之后就好像取消了戒严令似的,认为这些有问题的人都没有事了。那时好像没有提到“平反”两个字。我记得组织上没有下什么文字结论。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来了,那些当将校的同学们表情严肃,等待毛主席讲话,我院的同志也参加了。毛主席讲的话大都记不得了,只有几句印象深刻。主席说:“……一个人在肉体上挑个刺,总是要带动许多好肉,这一回审干冤屈了许多同学,我是整风审干的总司令,我要负责任,我现在向你们道歉。”说着随即举手向大家行礼,又说:“同志们不点头,我的手就放不下来。”这时只听到一片抽泣的声音。这次报告之后,生活气氛又恢复正常。
在审查运动中,剧院没有演传统戏,我留在部艺的时候,看到剧院演三个戏,一个是《穷人恨》,是张一然演主角;一个叫《上天堂》,由王一达演主角;还有一个新编戏叫《人变鬼,鬼变人》。这是反映审干生活的。这是演传统戏之后第二次演的现代戏。
审干之后,气氛变正常了,延安的干部晚会又要求看传统戏。我记得审干后的第一次演出,就是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演《群英会》。因为人们已有多时没有看戏,所以这次的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七、创作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
延安培养了一批京剧爱好者,有些机关有业余小组,最大的小组是中央党校的俱乐部,其中有许多是当过将军的,如索立波同志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严重迫害民主人士,有的被暗中刺杀。党校的齐燕铭和杨绍萱同志就编了一个剧本《逼上梁山》,作为古为今用的一种历史反映,由俱乐部的京剧爱好者们排演。这些京剧爱好者都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政治水平高,理解能力强,练功又刻苦,经过几个月的排练和修改之后,该戏一演出就轰动了延安。毛主席看了这个戏,大为赞赏,写了封信祝贺演出成功。这个戏后来交由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我也扮演了其中的角色。“文化大革命”之后,《逼上梁山》也由齐燕铭同志重新改编过,由马彦祥导演,是在北京京剧院排演的。
研究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又受到这个戏的影响,创作了《三打祝打庄》。为了写这个戏,由院长刘芝明领导,召集党校一些富有军事政治经验的学员一起来研究、讨论这个戏的题材和主题。毛主席认为《水浒》中“三打祝家庄”这段故事最有辩证思想。它的主要故事情节有宋江的攻坚失败,失败之后,就设计瓦解敌人的三庄联盟,最后又用里应外合的策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阶级斗争的武装冲突中,这类例子是不少的,但是要具体地生动地组织到戏里去,把现实的生活提炼为京剧的情节,以“唱念做打”的形象把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作为一个戏剧在舞台上表现出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大家讨论之后,由李伦、任桂林、魏晨旭三同志执笔,由王一达导演。我扮演钟离老人,魏静生扮演石秀。这场戏只有两个人,我们自己导演。这个戏第一次演出时,要演两个晚上,每晚四个多钟头。后来经过修改压缩,改为一个晚上,演出效果和《逼上梁山》一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也写信来赞扬,祝贺成功。可惜信件在延安转移中被遗失。这个戏不仅是剧院的保留节目,各解放区都演。在戏曲改进局时期,田汉同志又改过一次,到庆祝国庆十周年时,我和李伦又修改了一次,时间又压短了些。“文化大革命”之后,魏晨旭同志邀我和王一达、李伦、任桂林讨论改写这个剧本,后来没有写成。之后我到长春换牙,一个人修改了这个剧本,没有机会和大家商量,担心会意见不一而且有擅自作主之嫌,所以就没有拿出来。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这两个戏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在政治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认识上起到提高的作用,对全国新编历史剧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运用传统戏曲演现代戏是现实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在延安还写过现代戏《钱守常》(由我自己演出),也写过新编历史戏《宋江》。下山之前,毛主席警戒我们不要被“糖衣炮弹”打倒,因此,我和任桂林合作写了《李闯王进长安》,在联大时演过,在天津演过,在北京文代会也演过,当时效果还好。但我感到情节单薄,政治倾向太浓,还是不太满意。在革命的圣地延安,我们创作演出了一些现代戏,与民国初年演时装戏的艺人不同的是,我们的现代戏在题材内容的选取上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的,是在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自觉地对京剧进行的改革。
八、下山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用全国力量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会议期间,延安平剧院多次去杨家岭礼堂演出,节目有《三打祝家庄》和其它传统节目,以活跃文娱生活。此后不久,日本投降,为了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破坏和平的阴谋,党中央决定,毛主席飞赴重庆谈判。毛主席重庆谈判回来后,一次,平剧研究院在杨家岭演戏,我们在一个走廊里遇见了毛主席。我们问毛主席在重庆看京戏没有,怎么样?毛主席说:“蒋介石陪我看三天戏,最后一天没有去。”又说:“他们的技术比你们的高些,风格没有你们高。”我想,延安的京剧对象主要是首长、干部和战士。是他们的欣赏兴趣培养了我们的演出风格。至于技术,人家是科班出身,有深厚的功底。如果技术功夫又好,艺术修养又高,体会人物又深刻,风格就更高。毛主席看平剧院的戏,给我们很大鼓励,他总是看完戏才退席。
后来,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时局紧张。我跟剧院有秩序地疏散到绥德,没过多久,延安又来信,调我们回去。没过几个月,时局又吃紧,胡宗南再度进攻延安。为了消灭敌军,我们又有计划地撤出延安。
这时中央组织部把延安平剧院交由华北联大的成仿吾同志领导,由罗合如任院长,我任副院长。我们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到河北,一路行军,一路演戏。到阜平时,我们看到了周扬同志。周扬同志与我和罗合如同志谈话,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扬讲“如何理解生活”的一句话,他说,生活是政策的生活。这句话给了我新的启迪。行军到了西柏坡暂时休息,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那里。陆定一和肖山同志来看望我们。陆定一同志说,延安平剧院的任务就是搞戏曲改革,演现代戏,影响旧班社。
我们到了河北正定后被编入华北联大。华北联大名义上还是军事编制,每一个系是一个中队,平剧院也成为一个中队,住在束鹿的小李家庄,离辛集市不远。在那里,我们常去部队演出。
从1938年春到延安后一直到华北联大的生活是最值得我这一生怀念的。京剧在延安时期的作用,一是改造旧形式,为抗战服务起积极有效的宣传作用。二是演了相当一个时期的传统戏,活跃了延安干部、群众和中央领导的文娱生活,很受欢迎。三是创作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开辟了京剧艺术上的政治方向。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是延安京剧运动的过程,虽然当时没有提出“三并举”,但总的说来和新中国成立后对京剧改革所提出的方针“三并举”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梁一红)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