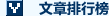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黄花会议
解绍德 程广安 解启磊口述,史扬龙 李传玺 陈劲松整理
导语:追寻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源头,绕不过安徽肥西的偏僻乡野—黄花大队,以及在那里召开的“黄花会议”。1978年,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江淮分水岭地区更是旱情严重,大部分田地绝收。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基层领导,体察民情,听取民意,于9月15日晚,在柿树岗公社黄花大队召开全体党员会议,本意在布置借地,种“保命麦”,没想到这次会议成了肥西县包产到户全面开花的源头。本文请当时参加“黄花会议”的三位老同志,详细讲述了“黄花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一、解绍德(今年74岁,时任黄花大队党支部书记,黄花会议的主持者):
还记得那年水塘干得底朝天,水田都裂出了一道道手指头宽的缝子,旱地更不用说了。夏秋季庄稼基本旱完了,而且来年小麦、油菜什么的根本种不上,因为牛根本犁不动地。这个时候省委号召各地借地给农民种保命麦,于是9月15日晚,区委书记汤茂林召开大队全体党员会议,开始布置这个事。
那时大队没有专门办公的场所,但我们这儿有个社办的黄花油厂,汤茂林来我们这儿蹲点就住在油厂,所以那天晚上的会议就是在油厂的南仓库里开的。会议是晚上8点多钟开始的。为什么要搞这么迟?是因为白天大家都还在地里干活,到这时才能吃过晚饭。
黄花大队有11个生产队,1800多人,24名共产党员。那天晚上开的是全体党员会,有一名党员不知什么原因没来,实到23名党员,加上区里、公社的6名领导,一共29人。6名领导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区委副书记张玉兰、山南公社副书记秦世民、山南公社党委委员廖自春、汤书记秘书权巡友、柿树岗公社武装部长权跃山。油厂南仓房的东头放有一张小方桌,桌上一盏煤油灯,我就坐在汤书记左手边主持会议,他的右手边是秘书权巡友。那天有好几个议题,但第一个就是借地种保命麦。省委当时下的指标是借给每人三分地,称之为保命田。其实,在省委决定之前,汤书记在我们这儿靠河边的汪祠生产队已悄悄试点,借地给农民秋种,每人两分地,那儿秋种干得好,可惜借的地太少。正因为有汪祠生产队试点,汤书记心中有底,当时开会前我们预先商议好了,把大部分地都借出去,借给每人一亩田种小麦,五分地种油菜。
汤书记坐着讲的,他喜欢抽烟,但那天他讲话时只抽了一根。他主要讲省委借地种保命麦的意义,就是稳定民心,那年夏秋粮食收得少,来年再没有收成,就都得去要饭,一定要下决心,吃点苦,把麦子油菜种上,这样来年午季才有希望,党员民兵一定要带头。他讲着,大家看着昏暗灯光下他的脸,仔细地听着,没有半个小时,简单得很,因为道理大家都懂。大家听了很兴奋。没有人有不同意见,所以一下就通过了。
汤书记还要求第二天所有蹲点干部以及村干部都下到各个生产队去,做好分田的思想动员工作。没想到当晚所有生产队社员都知道了,第二天他们也根本不要做思想工作和什么动员,一大早各生产队社员就忙着分田分地。这一分不得了了,省委让分三分地,我们原本定的是一亩地小麦、五分地油菜,这已经大大超过省委的要求。可他们倒好,这一分就挡不住了,干脆按人口呼啦啦地把田地都分了,包产到户了。我们村干部没制止也没办法制止,汤茂林也去生产队了,他也不制止。我们是9月15日晚开的会,第二天开始分的,两天时间把全大队2535亩地分完了。老百姓就开始锹挖榔头打,全家老少齐上阵忙乎开了。为了推动其他公社和大队的进度,9月19日,汤茂林居然把区里其他公社的书记都喊来了,在黄花开了一次现场会。9月20日,黄花大队的做法轰动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073个生产队。全区分田分地,一片忙碌,现场会变成了动员会。这些做法,与当时的政策要求不合啊,于是称汤茂林为“汤大胆”就这样叫开了。
其实汤茂林成为汤大胆是有原因的。听说这之前与山南区相邻的官亭区农场大队老庄生产队已经开始偷偷分地了(那时我们真不知道),他那时在官亭区当副书记,可能对他们的收成有所了解,觉得还是分干的好;还有就是他随身带着收音机,大概总能听出上面的一些精神;还有就是当时县委书记常振英在不远的双龙生产队蹲点,他俩常凑到一起喝茶呱蛋(土话,即谈心聊天),常书记对他总是支持的,所以汤才有这个胆气。当然,汤大胆真的有颗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
原来大呼隆(方言,一种集体劳作方式,形式隆重,效率低下,与之对应的是生产责任制)时,小麦每亩收200斤,有时还不到,这样一分,到第二年,虽然冬天仍旱得不行,但每亩收成竟然达到了400多斤,翻了一番,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二、程广安(今年72岁,时任黄花大队孙大郢生产队政治队长)
当时我们生产队也没想都分掉,只想地那么干硬,牛都犁不动,人也不一定能干得动。在每人借足一亩五分地之后,就这样对社员说,剩下的地,你们谁种谁收。于是有的人家要得多,有的人家要得少。
为什么当时没有按人口平均分?社员对多余的地也没有要求按人口平均分。一开始分时,虽然大家很高兴,但也都或多或少持有观望态度,对分多分少并不太在意,因为他们不知道上面让不让干,能干多长时间,也害怕一下要了很多地,最后挨批。
但不管分多分少,一但分到手了,他们都使出所有的劲拿出所有的家当干了起来。当时在生产队时,一亩地最多施20斤左右的磷肥,现在,好家伙,他们一亩地往往要施四五十斤。那时磷肥160斤一大袋,肥效好得很,9块多钱一袋。这个价钱现在看起来不贵,但那时候大家都没钱,这9块钱可不是好弄的,但他们为了多打粮食,就会想方设法去东挪西借。
正是由于肥施得足洒得多,到春天时小麦长得从没有过的好。过年后不久,好像田地里还有冰渣子,区里又在这里开了个现场会。第一次现场会开过,有的地方像这样干了起来,有的地方胆小,再加上县里出现不同意见,他们就更不敢分了。这次现场会就是告诉大家,田地分给私人种,庄稼长得更好,也没有出现什么倒退、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会开过后,我们生产队原持观望态度的、地没要够的人家,看到政策可能会稳定,看到要地多的人家今年会有大好的收成,会增加好多收入,于是开始吵着要按人口重新分地了。由于开始分时,只是考虑如何尽快分下去,把小麦油菜种上,时间匆忙,并没有进行好坏搭配、远近适宜和一家一户就便等因素,也给许多人家耕种带来了不便,有人吵着重新分,大家也都同意了。于是到1979年午收前夕又重新分了一次,开始按人口多少平均分,按一家一户就便,田地肥、瘠、远、近搭配来分,如果几户都差不多,那就只好抓阄子。当然田里麦子还是谁种谁收,收完之后,按照新分田地,各种各的。
后来有人写信反映说,分田到户毁了工农联盟和军队长城。当时省、地区部队领导来山南区当面指责汤茂林分田到户的“错误”做法,并责令改正这些做法,也是这个理由。他们说,农民分田到户了,收入增加了,家在农村的工人和子弟兵都不安心了,担心家中劳动力不够,分到的田种不了,都想回来了。其实从我们村当时情况来看,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远的工厂不说,就说我们自己的油厂,过劲得很,有工人二三十人,3台木榨,还加工稻子,就油来说,收的都是本地黄菜籽,每年都收五六十万斤,经过人工晒、炒、榨,出油率高,质量好。油厂香脚也很大(方言:市场大),不仅本地人喜欢,连稍远的舒城的人也来加工,丰收时换油的人排队都排好长,村里也是一年到头飘着浓浓的菜油香。那时厂里面的工人1块5毛钱到2块钱一天,我们队那时一个工算好的,也就值四五毛钱,工资是我们的三倍多啊,我们都羡慕他们,他们哪会看好我们,即使分田到户了,收入增加了也没他们工资高,何况有的家庭也还有其他劳动力。参军入伍的家庭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相反家庭日子好过了,会让工人和军人对在农村的家庭更放心,他们在外干得更安心。
我自己就是参军退伍的,对此有很深体会。那时能参上军可不得了,在部队干得好提个干,就是公家人了,即使没文化退伍了,也算见过世面经过革命大熔炉锻炼了,回来也能在当地得到安排和尊重。我是1969年底入伍的,1975年冬天退伍,吃亏就在没有文化。正是由于我在部队呆过,回来我担任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政治队长好像在其他地方没有,我们这里有,都是由在部队呆过的人担任的,他们同时还担任民兵排长。那时天天说有地富反坏右要搞破坏,有想搞资本主义的人搞倒退,由参过军的人担任政治队长和民兵排长,可以一下把这两个方面管起来,一方面搞好安保,一方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但我这个政治队长,在个别部队首长认为分田到户是倒退时,我为什么没有支持他呢?那时我家3口人,原本应该有5口人,即父母、我们夫妻俩和妹妹,可父母在过“粮食关”(即三年困难时期)时都饿死了,剩下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也幸亏后来搞了一段时间责任田,日子有所好转,保住了我的命。我是1972年在部队时结婚的,每次回来探亲看到家乡仍然那么穷,心中不是个滋味,现在又搞分田到户,跟当年责任田差不多,我为什么要反对呢?那天开会时,公社武装部长权跃山也在,他有把手枪,常常挂在身上,并时常对着大家,拍着身上的家伙,那天他就带着在,开会时,还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一会儿摆弄一下,弄得桌子咣当咣当响,在所有参会人中我以为他会反对呢,他就没反对;最主要的,我们大家就听汤茂林的,因为都觉得汤书记可靠可信。那时没有报纸,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大高音喇叭,但有时不响,上面的信息来得慢,或者根本就传不到,来蹲点的区委领导向我们宣讲上面政策,最掌握上面的精神,他吃住在我们大队,与社员一起生产劳动,想我们所想,听他的没错。
分田时,我们对“四类分子”也一视同仁,没有把不好的田地专门分给他们。“地富反坏右”,我们这里都是农民,没有右派,也没有“反坏”,只有“地富”。那个时候好像在开始说要给这些人平反,不唯成分了,同时这些人都是一个家族的,不是的往往也沾亲带故,他们虽说是“地主”和“富农”,但也是自己苦累和勤俭持家挣来的。这些年除了按政策在子女升学招工入团入党等方面有限制,每年要叫他们出一些修桥修路竖电线杆等义务工,和帮我们跑跑路送送信外,我们也没怎么斗争他们,他们也没搞过什么破坏,也没表现出要复辟的样子来。我们把他们的子弟也当作普通民兵,不过不能当基干民兵罢了。这个时候更不能歧视他们了。
三、解启磊(今年70岁,时任黄花大队王小郢生产队会计)
那时我们这个大队与周边其他队比起来,还算是稍微好些的。一个工有四五毛钱,每人每年可以分到500多斤口粮,五六斤油。鸡可以养,一般每家能养五六只,养多了,没东西吃,鸭鹅不给养,猪能养,只要你有东西给它吃。生产队那时每年有上交的生猪任务,我们这儿,一个队往往要上交四五头,就从养猪人家买,怎么买?不是直接给钱,而是补助粮食。补助粮食挨家挨户凑,集体时难干,人心不齐,凑粮难,为凑足粮,我们还和社员打过架,搁现在都很难想象。一头猪长到130多斤就可以了,这样的猪能补700斤稻子。那时好稻子每百斤在9块5毛钱,就是那个一袋磷肥的价钱,按这个价格算,一头猪也就是70块钱这样子。
我们大队干部一年的工分待遇好像也比其他队多些。每个生产队100个工提一个工给大队干部。这样大队书记一年可以有5000多分。折算一下,也就是他们一年的工资在250块钱上下。
每个生产队平均有3条大牛,一条小牛,就这些“活”的大农具分田时不好分。分田时每个生产队也按照大牛的头数,把农户相对分了几个小组,这样牛就能分开了。这样分实际上就是几家伙一条牛,牛在谁家干活那天就谁家放。开始,大家都想早点把地种下,有点不顾牛累不累,牛放得时间很短,也不管它吃没吃饱。一段时间后,有的队的牛瘦得不像样子了。那时地虽然分了,但大家都在强调不能损害集体利益,看牛瘦成这样子,生产队急。后来大家也明白了,你糊弄牲口,虽然它们不能讲话,但糊弄到最后,受害的还是每家。后来大家就有个约定,第二天在上家把牛交给下一家时,如果牛肚子是瘪的,不接。
“黄花会议”后,我们这儿社员种地积极性高,庄稼长势很好,又开了两次现场会,名声就出去了。对我们的做法,当时争议很大,支持的、反对的都有,也引起了省委的注意。1979年5月21日省委书记万里第一次来山南视察时,原本是来看黄花大队的。没想到万里轻车简从,直接到山南来了,省委居然没有通知县里,自然也没有通知汤茂林。那时不像现在每家都有电视,新闻联播差不多天天都能看到省委书记,不要说干部,就是普通老百姓都能认识省委书记。就是这个没通知和不认识,万里到区委时,汤茂林居然不在,大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汤书记秘书权巡友倒是在,但他不知道来的人就是省委书记万里。常来这里调研的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跟着在,权秘书认定是省委来人了。权倒是机灵,他把万里带到同在一个集镇上,相隔不远的山南公社,把万里交给了区委副书记兼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然后开始四处找汤茂林。他认为汤茂林那天是回聚星家里了,就搞了个拖拉机头,叫人开着去找。其实那天汤茂林是下队去了。自然在家里找不到他。
好不容易找到汤茂林,并让他赶回来时,万里已经被王立恒引到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开座谈会去了。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万里对分田到户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比小井庄干得早干得彻底,他们敢干也是因为在我们这儿开了现场会,受了我们的启发。万里是想来我们这儿看的,就因为汤茂林的不在错过了,最早包产到户的这朵大红花戴到小井庄去了。这也是大家经常说的包产到户“黄花开花、山南结果”的由来。
采访后记:虽然包产到户这朵大红花戴到山南小井庄去了,但就包产到户史来说,“黄花会议”怎么都绕不过去。虽然“黄花会议”只是布置一个村借地种保命麦,但它在包产到户史上的突破意义和示范效应将永远被后来人牢记,这其中作为会议实际主持人和包产到户操作者的汤茂林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者单位:史扬龙 民建安徽省委员会
李传玺 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陈劲松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
(责任编辑 樊燕)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邓园”往事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