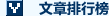中央红军情报侦察工作纪实
董小林
中央红军早在初创时期,就注重做情报工作。南昌起义后,由于起义军在南下广东时未注意对沿途敌情的侦察,致使部队遭到国民党军围攻。鉴于这一教训,朱德、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在军中设立特务队,专事敌情侦察搜集工作。但受客观条件限制,这种情报工作的方式还比较原始。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各项条件的改善,加之战争规模扩大对情报保障要求的提高,中央红军的情报工作在战争实践中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在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严密的组织机构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中央被迫迁往武汉。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下设特务科,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分共”,中共中央被迫转移至上海租界内。11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关于调整中央组织机构的决议,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分为特一科(总务科)、特二科(情报科)、特三科(行动科)、特四科(交通科)四部分。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在搜集情报、打击敌特、惩治叛徒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情报机构上的成功实践,对各地红军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
1930年是中央红军发展历程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红军正规兵团—红三、红一军团及红一方面军相继组建,作战方式也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为即将到来的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以国民党军主力为主要对手的大规模作战准备了条件。为适应形势发展,同年8月,中央军委(193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事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在参谋部下设谍报科、交通科,负责有关国民党军情报的搜集传递工作。然而,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与江西苏区相距千里,加之两地此时尚未建立无线电联系,靠人工传递的办法难以实现重大情报的及时互通共享,因此加强苏区红军自身情报机构的建设显得尤其重要。
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镇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中央局军委)亦于同时成立,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苏区中央局军委成立后,随即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将红一方面军机关改为军委机关。因此为加强苏区红军的情报工作,在军委总参谋部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下设谍报科,作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业务领导机构,另有第一次反“围剿”后刚刚成立、负有对国民党军电台侦听功能的无线电队;5月,无线电队扩编为无线电大队;9月,无线电大队进一步发展扩大为无线电总队,队长是人民军队通信兵事业的重要创始人王铮,政治委员是翁瑛,下设专门从事监听侦收工作的侦察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成立,谍报科改称侦察科,并将无线电总队侦察台的业务和设备划归其下。1932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新颁布的编制表,军委总参谋部侦察科改为情报局,即第二局,故称军委二局,下设侦察、谍报、管理三科,专做敌情侦察工作。1933年5月,中革军委总司令部(1932年12月,中革军委决定统一全军各部门名称和各级职务人员称谓。据此,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改称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从前方回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总司令部第二局负责情报工作,又称后方二局,局长由中共情报战线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担任;以原总司令部的部分人员在前方另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下设第一(作战)、第二(情报)、第三(管理)局和通信主任,第二局又称前方二局,局长为曾希圣;同时,为克服部队获取情报“依赖白区和边区的党的秘密工作”和“依赖上级”的问题,加强对部队侦察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在主管作战的第一局下设侦察科,并在团以上各级司令部机关设立侦察科,下辖侦察员或侦察队。经过此次整编,中央红军初步建立起了从总部机关到作战部队的情报工作系统。
1934年初,红军总部机关与中革军委机关合并。与此同时,前方二局与后方二局合并成为新的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为曾希圣,副局长为钱壮飞,下设专职破译的第一科、负责侦收的第二科、进行校译的第三科和做谍报工作的第四科,负责向军委总部首长提供战略层面的情报;侦察科仍设在第一局,负责指导部队侦察工作和对各级上报的情报进行汇总。除司令部系统外,政治部系统做兵运工作的敌军工作部门和负责锄奸防特的保卫工作部门,也兼有搜集掌握敌人内部情报的责任。这样,经过不断调整充实,中央红军形成了体系完备、组织严密、职责明确的情报工作机构。
强大的侦察能力
除了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报告敌情这一渠道外,中央红军获取情报还有谍报侦察、部队侦察、有线窃听和无线电侦听破译等多种途径。谍报侦察、部队侦察属于传统侦察手段,有线窃听和无线电侦听破译则是近代以来才在军队中出现的技术侦察手段。
作为古已有之的侦察方式,谍报侦察、部队侦察在中央红军情报工作中依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里除了技术侦察装备不足的客观因素外,还因为谍报侦察、部队侦察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一是更加准确可靠,比如打入敌人内部高层的谍报侦察,往往能够获得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核心机密;二是更加详细具体,比如战斗发起前,除了上级下发的总体敌情通报外,一线部队还需派出侦察人员搞清当面的地形、敌情,才能更有针对性地部署兵力。据当时在红军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回忆,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派人伪装到敌人阵营中去,获得敌人情况;捕捉俘虏,审问敌情;搜集文件、报纸,分析敌人行踪;从起义、俘虏过来人员中了解敌人情况;在敌、友军驻地居民中进行调查获取敌人消息等”。实际上,中央红军一直十分重视这些传统侦察手段,除前文已述的建立从总部到团一级部队侦察工作的领导机关和侦察力量外,1933年6月,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参谋长叶剑英还联名发布了《健全红军的侦察工作》的训令,指出“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这里强调的侦察工作主要是指谍报侦察和部队侦察,因为无线电侦听破译在当时尚属核心机密,知情范围仅限于总部机关的少数高级领导人。
与谍报侦察、部队侦察相比,技术侦察特别是无线电侦听破译在那个年代算是“高科技”,也是中央红军情报工作体系中最神秘、最精彩的部分。19世纪末,无线电技术面世。20世纪初,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将无线电发报技术和摩尔斯电码用于军事信息传递,建立无线电通信。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军事情报技术:即无线电侦听、侦收和密码破译。
一开始,国民党军虽然在无线电通信中采取了加密措施,但由于其内部派系林立,各派为相互防范往往另行自编密本,导致难以实行统一的机要密码制度,加之军纪不严,管理混乱,通信人员思想麻痹,经常在电报联络中用明码直接呼叫,这就为红军进行无线电侦听创造了机会。据人民军队通信兵事业另一重要创始人刘寅回忆:“白军由于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所以他们在无线电通信中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要相互询问:‘QRC?’(你们驻在何处?)‘QRC……’(我们驻在……)白军调动之前,我们经常可以收到他们彼此之间这样的电讯:‘请将电报发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发。’‘请即停止联系,我们立即出发,X小时后再见。’”“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
后来,由于国民党军在历次“围剿”中有不少电台被缴获,技术人员被俘虏,特别是宁都起义后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携带电台加入红军,因此国民党军开始重视无线电通信保密,普遍采用了密码通信。在以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为代表的“红色听风者”的不懈努力下,军委二局很快摸清了国民党军的编码规律,开始不断破译密码。此后,意识到通信泄密的国民党军虽然不断更换密本,加大编码难度,但始终摆脱不了被军委二局破译的命运。据统计,从具备破译能力开始,到1934年7月,军委二局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本400余本,其中包括一部分高度复杂的特别密码本,曾希圣也因此被称为能够读懂“天书”的人。长征开始后,随着中央红军频繁的行军战斗,军委二局对国民党军密码的破译也达到一个高潮,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100%。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军委二局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种。
这样,国民党军在中央红军面前就成了透明的“玻璃人”,几乎无密可言。对此,刘伯承元帅曾有形象比喻,他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关于军委二局的破译能力,可从一个例子中窥见一斑。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见到了国民党军将领李默庵,于是就随口念出这位他当年的黄埔学生作过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李默庵闻之大惊失色,因为这首诗是1933年他参与“围剿”中央苏区时,目睹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被红军歼灭,两位同僚一死一俘后的感怀之作,并用师部电台通过密码电报发给了在上海的夫人,以表达自己那时的心境,此后从未示于他人。周恩来如实相告,是红军截获了这份电报并破译出来的。得知这一真相后,李默庵除了震惊外,可能更多的是惆怅与失落吧。
特殊的功勋业绩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有一段关于情报工作重要性的精彩论述: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作为一位刚刚经历长征,将中央红军带出险境、绝境的军事统帅,毛泽东是有感而发,是对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概括。
为谋取情报优势,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红色情报人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身处龙潭虎穴的谍报人员,与敌人斗智斗勇,冒着随时被杀头的危险将一份份情报源源不断送出;军委二局的技侦人员,为随时掌握国民党军情况,长年值守在机房,终日与枯燥的数字代码打交道,为破译敌军密码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可以说,出色的情报工作,是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取得伟大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关于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可通过几例加以说明。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计划先打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但该敌一直龟缩在堡垒工事中,难以攻击。红军在隐蔽待机20多天后,通过无线电侦听,从该路敌军公秉藩师电台与后方留守机构的对话中,得知该师即将离开富田向东固发起进攻。于是,红军在东固地区设伏,一举歼灭了公秉藩部第二十八师,取得了首战胜利。此后在准确情报的支援下,红军从西向东横扫,连打四个胜仗,长驱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老红军郭化若说:“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我们用无线电台侦听,对敌人情况了如指掌,有了主动权,仗打得更顺利。”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利用缴获的敌军密码本,由无线电技术人员曹丹辉截获并翻译出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重要情报,从而为红军主力从闽西千里回师、做好反“围剿”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
第四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利用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提供的国民党军部署调动情报,先后在东陂、黄陂、草台岗等地区设伏,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全部、2个师大部,其中包括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师,彻底打破了“围剿”。为表彰军委二局的特殊贡献,在1933年建军节到来之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授予曾希圣二等红星奖章,授予曹祥仁、邹毕兆等人三等红星奖章。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为其制定了旨在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重兵和大量装备,采用逐步推进、四面合拢的办法,在瑞金周围构筑数十道由碉堡和铁丝网组成的封锁线,先抑留红军于圈内,进而一举聚歼。获取这一绝密情报后,中共地下党员、谍报人员项与年历经千难万险将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从而促使中央红军在敌人形成合围之前踏上了长征之路。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四道封锁线,虽遭受重大损失,但仍按照原定计划,沿湘黔边北上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就在沿途布置重兵,张网等待。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地处湘黔桂交界处的湖南小城通道,当天深夜,军委二局截获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调动兵力堵截围歼红军的绝密情报。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在严峻的敌情面前,毛泽东放弃北上、进军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了采纳,使中央红军免去了覆灭之险。
四渡赤水期间,重回军队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下,在川黔滇交界地带的崇山峻岭和江河激流间,来回穿梭,反复调动打击敌人,直至取道云南北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这一切,都离不开军委二局准确有力的情报支持。第四次渡赤水后,甚至发生了军委二局利用“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为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争取时间的神奇故事。毛泽东后来多次称赞军委二局是“好的二局”,并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责任编辑 王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