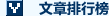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张凯峰
近代中国自从被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列强除了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经济利益之外,还通过开办学校进行文化教育渗透。
一
民国初年外国在华办学的重灾区要数东三省。
日俄战争以前,东三省外国办学以俄国为最。1898年,沙俄沿中东路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共400余所。不过俄国学校主要招收的是铁路员工的子弟,还有部分沙俄的地主、商人、资本家、军官的子弟,很少招普通学生。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人开始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若干公学堂,吸收中国学生入学。民国初年,由于东北社会动荡,教育经费削减,学校归并萎缩。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所办的学校乘机扩展,大批吸纳中国学生。1920年,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各地创办或控制的各类学校已达260所,学生人数为3483名[1]。
日本关东厅的教育方针是“把中国人同化于日本”,培养出一批懂日本语的中国人,“以便于我们的公私事务”[2]。为了贯彻同化中国人的教育方针,日本人所办学校中禁止学生阅读中国历史与地理,而授以日本历史和地理。
1923年,奉天省视学罗振邦、邵进阶参观南满中学校之后,报告说:
其所教授之历史,系采用日本文部省所规定之中学东洋历史。内容组织完全以日本为主体,年代纪元则以日本为本位,国际关系则以日本为中心,史事则又中国极简而日本极详。此等历史使中国学生读之,自不免使彼等徒知武尊明治,日本天皇之如何英武、变法维新,日本皇国政治之如何进步、败中胜俄,日本帝国国势之如何发展,而茫然古代文明灿烂之中国矣。……其所教授之地理则系该校自行编印者,内容简略异常。关于中国疆域之广袤、省道之区划、形势险要、商业物产,种种要项,多付缺如。即以东三省论,惟有南满沿线各商埠县分稍加详释而已。以此等地理而教吾中国学生,自不难使彼等徒知日本所谓关东的范围内之事,日本在南满经济之如何发展、势力之如何雄厚、经营之如何完备,而不知有所谓奉天与中国矣。
日本在东北搞的教育显然严重干扰中国的民族认同建构。罗振邦、邵进阶在报告中指出:
凡我国之青年入南满中学受教四年之后,国家观念及中国完全化为乌有,仅知以衣食住生命为重。此种教育如果普及于我东省后,恐几十年间吾东省之一般青年便不知中国为何物而己之为何种人矣。将来此种青年只可如印度人之充当巡捕,在世界上宁复有立足之地。[3]
1923年,奉天教育厅长谢荫昌曾著文表示担忧:
今南满铁道用地横贯我之中心,其所设附属公学,以日本语言文字编写历史、地理教我儿童,年号则用‘大正’,唱歌行礼则三呼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之声彻于霄汉。我之昆季谓他人之父兄为父兄者,有不为之痛心疾首乎!坐视我之子弟沦为外人而不思援手,十年二十载之后,其亡国灭种之政策日益深入……故奉省教育上应著手从事着,即收回南满铁道用地国民教育权是也。[4]
他在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提案要求: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省政权所及之地域对于奉省人民施行师范教育、小学教育。此案获得全体通过。奉天教育厅,派调查员数人调查两路各站,结果一致认为应予收回教育权,于是一面筹备手续一面发表言论。“日人色然而惊,既令领事至交涉署质问有无对于教育不愿日人之协助,又遣代表赴厅协议教育事项,表示绝不放弃在奉设立公学堂及师范学堂之意”[5]。对于中方所指控的侵犯教育权之事,日本报纸“几欲牺牲全幅而辩护之”[6]。
为抵制日本的教育扩张,谢荫昌支持并帮助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该组织曾计划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成立调查日本文化侵略的委员会,向日本国民和政府官员申述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以唤起世界舆论,唤醒中国教育团体。旅顺大连两地已鲜有华人所办学校,惟大连中华基督教会所办的附属小学“尚有可观”。奉天教育厅于是给予特别扶持,每年拨给奉洋五千元,以图振兴。
1924年3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与谢荫昌会谈,谢明确指出:“一国之国民教育,根本一国历史之精神。无论何项国家,决无他国越俎以救其国民之理。……中国人民而施以贵国之国民教育,在贵领事于心安乎?”[7]
在各界人士推动下,奉天教育厅于4月11日宣布了收回教育权的决定,规定嗣后外国人在东北设立学校须经省教育厅批准并遵循中国的教育法规。在奉天教育会年会上,谢荫昌代表省教育厅宣布:禁止中国儿童到日本学校读书,小学教师中的外国公民必须退职。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还会同谢荫昌向日本总领事及满铁地方部交涉,要求尽快交出南满铁路附属地教育权。与此同时,南满教育协会等教育团体号召学生罢课,并敦促地方政府进一步限制日本教育势力的扩张,建立能够取而代之的中国学校[8]。
《中国青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最近奉天的官厅教育界不正在进行从日本争回南满沿线的教育权么?张作霖纵有一万个不是,在这一件事上,应当全国一致的督促他,援助他。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听任外国人自由办理,这是又一次的民族革命呢。”[9]
但是奉天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还是迫于日本的压力而终止了。奉方屡次交涉,日方并没有正当的答复。日本关东厅教育当局否认问题的存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之教育,并无何等强制力,一任各该地方居住之华人自由决定,丝毫于中国教育无碍。……中国方面实无亟亟于收回之必要,盖其权利实未被夺,而南满铁路亦无被人收回之权利可言。”
南满铁路公司态度更加强硬,其教育当事人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说道:“一国之文明,亦必因他国之文化侵略,而后能达成其目的。理应感谢,何得反对?故南满铁路方面,不论中国方面如何主张,决不许其收回。纵令中国正式前来交涉,亦必断然拒绝之。”[10]
谢荫昌提出由中方对这些学校“计费偿还,收回自办”,日方没有同意。奉天当局遂向日本总领事提出的折中方案:日方自明年起停止招募公学堂学生,但专门学校仍可照从前办法办理。也被日方拒绝。最后谢荫昌因为交涉棘手而忽然辞职。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奉天东报》与日本人所办的《盛京时报》作针锋相对的辩论,言论上不无涉及日本要人之处。日本领事因此要求取缔该报,日本宪兵也到报社骚扰,《奉天东报》不得不暂行停刊。
不过,这次运动多少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五分之二外国学校的中国儿童回本国学校就读。一些外国人办的学校(不包括日本)被关闭了,保留下来的学校则被要求必须执行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法规。
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并且把创办学校当做一种有力的传教手段。到20世纪20年代,教会学校已经成为一个覆盖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多种专门教育的、独立的教育系统,不受中国教育部门管辖,也无需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到1926年,新教在华办学约6000所,包括16所大学,200所中学,5000余小学,学生约30万,天主教办学约9000所,包括3所大学,200余所中学,其余为小学,学生约50万。合计教会学校已达15000余所,学生总数约80万[11]。
但是这种教育对近代我国民族的教育是一种干扰。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向爱国学生宣布:“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12]于是教会学校中的学生,“国耻纪念会、外交后援会可以不开,礼拜万不能不做;中国报纸、中国杂志可以不看,查经班不能不上;国事纪念日可以不放假,而圣诞节硬要牺牲一个星期……”[13]
教育家陈启天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宗旨至少要培养本国国民,延长本国国命,光大本国国运。任何特殊教育宗旨不可与此国家教育宗旨冲突,致减少国家教育的效率,抹杀国家教育的根本。”[14]
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族认同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社会对教会教育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规定“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15]。
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运动纷纷而起,要求反对教会教育和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1924年7月到10月,数个学界重要团体会议宣告反对。少年中国学会第五届会决议纲领中有“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语。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发起收回教育权的运动,痛叙外人借传教而办教育之非。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通过了请求教育当局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议案。全国省教育会第十次联合会上有代表提议两案:一、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均获通过[16]。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由于有些教会学校干涉、禁止学生参加运动,反对教会教育之声更加激烈,有些学校发生学潮,许多教会学校学生退学。比如上海圣约翰学生全体签名退学。河南开封的安德烈学校学生也发出退学宣言,一律迁寓客栈。
新申学院在报纸上通告外国人所设学校离校学生,1925年秋季招考时优待脱离教会或外国人设立学校学生:凡在此次五卅惨案脱离教会学校,或非教会而为外国人设立之学校之学生来院肄业,经人证明得免入学试验;凡在教会学校一级之学生有二十人以上,来院肄业者本院得视察情形另开一级教授;离校学生来院肄业时均照院章永远减收学费五分之一。
上海乐益中学在招生广告中声明“本校为补助收回教育权起见,凡各教会中学退学学生来本校肄业者,得免考入学,按其程度插入相当年级”。上海大学暨附中招生时也表示凡因此次五卅运动而退学之教会学校学生“一经证实即予免考收录”。
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为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17]。
在华活动逾50年的美国圣经会报告说,因为教会学校新生寥落,且多数教会学校不再以圣经为必修科,1925年新旧约在华销量骤减[18]。
1926年10月,国民党北伐开始了,反文化侵略运动越发高涨,湖南各教会学校无不发生风潮,各省纷纷要求取缔外国学校。国民政府则颁布了严苛的《私立学校规程》: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须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私立学校之设立、变更、停办均须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私立学校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组织、课程、教授时间及其他一切事项,均须根据现行教育法令办理,校务、教务各事项,须遵照定章及教育行政机关命令,随时呈报;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私立学校办理不善,或违背法令者,政府得解散之。
在这样的浪潮之中,广州岭南大学被改组后交华人自办。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卢爱德引退,将校务交与华人。拒绝学生取消圣经课和礼拜要求的岳阳湖滨大学停办。长沙各教会学校也纷纷停办。在江西九江创办了40余年的南伟烈学校被更名为私立同文中学,向教育厅呈请立案,嗣后不再受教会之节制。各地华人自办的公私大中学校纷纷表示对于从教会学校转学的学生特别优待,酌减学费。
1929年8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新的《私立学校规程》,除了重申不得由外国人担任校长和不准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外,还特别强调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劝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19]。
大部分教会大学主动作出回应:增加国学课程和学分;一切学科以国语教授为原则;提高中国教职员工比例;取消强制读经和礼拜;向政府申请立案注册。个别不愿改造者,或者宣告停办,或者被政府勒令解散。
《中国教会大学史》中这样说:“20世纪的年代的事件结束了一个时代,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人管理的宣传外国教义的学校了。由于中国人取得教会学校的最高行政职务,同时在教师队伍中,中国人已经成为多数,因此在1926—1928年中国化的进程突然加快了。教育成了学校的主要目的,传播福音只能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
注释:
[1]《南满日本学校之新调查》,载《教育杂志》1920年第7期。
[2][3]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2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2页,第909、908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沈阳文史资料》第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版,第39页。
[5]心史:《收回教育权》,载《申报》1924年4月26日。
[6]《奉教育界收回教育权之运动》,载《申报》1924年4月23日。
[7]杨光主编《皇姑文史资料》第19辑,政协沈阳市皇姑区文史委员会2007年版,第504页。
[8]《教育界消息》,载《新教育》1922年第3期。
[9]但一:《广州三一学生的民族革命》,载《中国青年》1924年第29期。
[10]《举国瞩目之收回教育育权问题:奉省之办法,日人之态度》,载《教育与人生》1924年第32期。
[1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12]杨效春:《基督教之宣传与收回教育权运动》,载《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8期。
[13]伦杰:《教会教育与中国》,载《行健》1924年创刊号。
[14]陈启天:《我们主张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与办法》,载《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8期。
[15][17]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3页,第784页。
[16]保真:《反对教会学校》,载《圣教杂志》1926年第6期。
[18]《美国圣经会圣经销数之报告》,载《申报》1926年2月5日。
[19]《私立学校规程》,上海法学编译社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法令大全》第七册,会文堂新记书局1931年版。■
(责任编辑 陈晓红)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