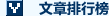东京审判:审判日军在华战争罪行
赵玉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同意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虽为战胜国之一,却在战争中饱受国土沦丧、国民流离之苦。为惩罚战争罪行,同盟国先后在纽伦堡和东京举行了两场先驱性的国际军事审判。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在华所实施的种种罪行,以及发动战争的个人,一并被予以检控和定罪,由日本发起的这场战争的全貌也由此昭然于世。
战后法庭的筹备与设立
18世纪以来,“战争非法”,以及要对侵略战争发动者追究刑责的观念,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最终在“二战”后的战犯审判中得到了司法实践。
对于如何处置侵略战争的发起国,同盟国原本存在不同的主张。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于逮捕战犯后尽快处决,而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过于严厉的惩罚不仅无助于铲除战争的温床,还只会埋下怨恨的种子,只有用审判这样的文明手段才真正有助于防止战争再起[1]。最终,同盟国就任用职业法官来审判战犯的立场达成一致,先后设立了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远东小委员会,并确立了对德、对日审判的方案。后者内容包括建议同盟国在整个亚太地区展开战犯的起诉,并由其中一个法庭主要负责犯有反和平罪的A级战犯[2]。到1946年1月初,美国联络的八个同盟国都提名了推荐的法官。19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部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同盟国对日审判方针文件的授权下,命令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作为法庭检控部门,国际检察局也在各国检察官抵达之后在各国此前提交的被告名单基础上,迅速展开被告名单的最终确定和起诉书的起草工作。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启动亚洲唯一的A级战犯审判,这与同时期展开的B级、C级审判共同构成了战后亚太地区战犯审判的完整图景[3]。
东京审判被告名单[4]
战犯
荒木贞夫
土肥原贤二
桥本欣五郎
俊六
平沼骐一郎
广田弘毅
星野直树
板垣征四郎
贺屋兴宣
木户幸一
木村兵太郎
小矶国昭
松冈洋右
松井石根
南次郎
武藤章
冈敬纯
大岛浩
佐藤贤了
大川周明
重光葵
岛田繁太郎
白鸟敏夫
铃木贞一
东乡茂德
东条英机
梅津美治郎
永野修身
主要诉因
陆军的政治支配,侵略满洲
侵略满洲,虐俘
侵略满洲,政治宣传
陆军大臣,大政翼赞会,南京暴行
任首相时的日中战争,总动员
陆军追随者,南京暴行
侵略满洲,企划院
陆军大臣、侵略满洲、
卢沟桥事变、虐俘
大藏大臣,军事费
推举东条首相
陆军次官,缅甸暴行
满洲事变,暴行
南京暴行
满洲事变
南京、苏门答腊、菲律宾暴行
海军军务局局长,虐俘
日德关系
虐俘
太平洋战争
海军大臣,虐俘
日意关系,政治宣传
企划院总裁
太平洋战争
总理大臣,太平洋战争
侵略中国华北
中国作为同盟国之一,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有关惩治战争犯罪行为的国际法论证,并在追究日军战争罪行的时间和范围问题上展开了不懈的外交斡旋。原本英、美、澳等国虽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惩治德国暴行宣言的原则适用于对日审判,但认为追究日军的战争罪行应从珍珠港事件之后开始。这一点为中国所难以接受—若如此,则1941年以前日本在中国实施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种种暴行都将无法追究。故而,中国始终在各种外交场合坚持要求将追诉时间提前。1944年11月,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远东小委员会筹备时,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再次提出追究日军罪行时限为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即指示王宠惠、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向委员会提出申诉并声明:“我国虽于珍珠港事件后始对日宣战,但其效力应溯及既往。在未宣战以前之日寇暴行,同属违反人道与国际法惯例,不应另案处理,且若限于珍珠港事变以后之暴行,则日人在南京等地之奸淫烧杀掳掠皆不能提出,而分会之设立,对我将失其意义。”[5]最终,中国政府这一主张为其他同盟国家所接受—在东京审判的检方起诉书中,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追究时间定在了1928年,即法庭对日军侵华的事实调查从“皇姑屯事件”开始。
1946年初,中国向法庭派出的检察官和法官团队先后抵日。检察小组以向哲检察官为首,先后加入的成员有裘劭恒、刘子健、高文彬等人,展开了大量证据调查、文件分析翻译等工作。1947年进入个人辩护阶段后,向哲检察官向国内紧急申请,调派四位检察顾问加入庭审队伍。其中首席顾问倪征燠在被告个人辩护阶段对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出色的反诘。中国法官梅汝璈则负责了起草法庭判决书“日本对华全面侵略史实确认之一”的工作。
审理日军侵华罪行
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3日开庭至1948年4月16日庭审结束进入判决阶段,检方立证和辩方反证大约有1/3以上的内容,都与日军在华战争罪行相关。检方对于相关被告的指控除了反和平罪(对中国的侵略),还有普通战争罪(在中国各地实施的暴行)[6]。审判采用了一种混合式诉讼模式,以英、美法对抗式的诉讼模式为主,兼具纠问式诉讼模式的某些特点。法庭上检辩双方往往针锋相对,激烈辩论。
作为A级战犯法庭,审理反和平罪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内容。法庭宪章对这一罪名的定义为:“反和平罪,即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场经宣战或不经宣战之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为实现上述任何行为之共同计划或共同谋议。”[7]检方起诉书的55条罪状中前36项均与反和平罪相关。经过法庭精简为八项后,涉中国部分相关的罪状包括: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对东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发动战争的共同谋议;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实施对中国(满洲)的战争;等等。
上述“共同谋议”指的是英美法系中“二人以上就实行违法行为达成协议,法律对参与此协议之人追究其刑事责任”[8]。在东京审判中它被检方工具性地使用,目的在于方便地网罗尽可能多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反和平罪的具体罪行同被告的个人责任相关联。换句话说,通过“共同谋议”的指控,检方可以克服缺乏直接证据的困难,仅用间接证据就把被告圈入“策划准备战争”的指控。而“实施”战争,则是指控日军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发动与实施侵略战争。
尽管法庭宪章已经确认,不论宣战与否均可视为侵略,但辩方在法庭上仍坚决主张1941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武装对立属于没有宣战声明的事变,而非两国间的武力纷争。辩方更进一步表示:由于中日之间从未进入正式交战状态,中国士兵不享有作为俘虏的国际权利。中国检察官向哲针锋相对地反驳如下:“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9]最终法庭采纳了检方的主张,确认“中日间存在事实上的战争”以及日本负有“按国际法规对待中国士兵的国际义务”这两点,全面驳回了辩方的主张。
此后,检方向法庭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来还原九一八事件的历史真相。由于进攻东北乃是日本对华北甚至对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实施侵略战争的第一步,法庭对此进行了仔细查证并裁定:
有足够数量和确凿的证据显示“奉天事件”系经参谋本部军官、关东军军官、樱会成员及其他人等事先周密策划。包括[被告]桥本[欣五郎]在内的数名参与计划者在不同场合下承认了自身在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这一“事件”的目的在于为关东军占领满洲提供口实,建设日本所希望的“王道”新国家。[10]
法庭进一步认定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甚至全国挑起的军事行动都是一项长期密谋的重要部分:
当阴谋者们认为他们已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压倒国内的反对……逐步实行了为达到他们的日本统治远东这一最后目标所需要的攻击。在1931年,他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自1937年起,对中国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侵略并占领了许多中国领土,设立了仿效上述形式的各种傀儡政府,并且开发中国的经济和天然资源以供应日本之军事的和一般人的需要。[11]
最后接受判决的25名被告中,除了松井石根和重光葵两名被告以外,其余被告都被认定犯有反和平罪。而其中除了大岛浩和梅津美治郎二人,剩下的21人都被认定参与了侵略中国的阴谋。
正如前文所述,东京法庭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审判反和平罪行即侵略战争罪,但普通战争罪同样属于法庭管辖权范围。检方立证的15个阶段中,有4个与普通战争罪相关,而从最后的审判结果来看,法庭在对待战争暴行相关责任人的量刑方面也相当严厉。
普通战争罪的内涵在战前经由一系列国际条约而逐渐完善。这些条约包括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即《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其中规定了武装冲突中的基本规则和惯例;以及1929年各国签署的《日内瓦公约》,全称《战俘待遇公约》(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东京审判中,辩方主张日本不受这些条约约束,但被法庭驳回,认定日本有义务遵守《日内瓦公约》等一系列战俘待遇条约。
日本战败后,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文件烧毁工作,这使得有关战争暴行的取证变得异常艰难。还有一个难题则是,如何将发生在战场上的诸多暴行与地处后方、身居高位的28名被告联系起来。检方为此发展出一套策略来完成这些指控,即通过提交数量巨大的证据(战争罪行调查报告、目击者证词等等)来证明整个亚太战场上发生了大范围、长时间、高频率的战争暴行,而同一类型的暴行也在一地反复发生,由此来证明这些暴行不是军队在战地的随机肆虐,而是来自高层政策。如澳大利亚检察官曼斯菲尔德所言,“这并非个别日军司令官或士兵自发的行动,而是日军和日本政府共同的政策”[12]。
在有关中国的战争罪行立证阶段,调查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是中国检察组乃至整个国际检察局的核心工作。1946年上半年,国际检察局便派萨顿、莫罗等美籍检察官一同与中方人员几次赴中国实地取证,最终由萨顿带回了15名证人,包括南京普通市民和建立了国际安全区的外籍人士,如贝茨、马吉、魏特琳等人。他们的证词使得日军在南京实施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公之于世。检方的证据充分证明,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的至少6周里,日军大规模展开对中方战斗人员及普通市民的虐杀、强奸、抢劫、放火等非人道行径,日军也无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抗议,进入难民指定区域,强行带走妇女、男子进行强奸或枪决;日本政府和军部高层通过外交渠道和媒体均已知悉本国军队实施暴行的情报,这些人至少包括指挥南京战役的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副参谋长武藤章以及时任外交大臣广田弘毅。
从庭审记录来看,辩方对于检方提出的这些人证、物证,大多不予反驳,基本默认了这些事实。辩护律师布鲁克斯在询问检方证人、牧师马吉时甚至向庭长表示“证人非常公正”[13]。从他们的私人记录来看同样如此,辩护律师菅原裕在回忆录中承认,发生在南京的一系列事件“在日清[14]、日俄两场战争中是绝对不曾听闻的。对日本民族来说,这是比战败更悲哀的事实”[15]。另一名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也坦承“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南京市民所施加的暴行极为严酷这一事实是极难颠覆的”[16]。
最终法庭认定,被告松井石根、广田弘毅都对南京事件负有相应的指挥官及阁僚责任。两人最终都被判处死刑。值得注意的是,松井石根在所有罪状中仅仅是因为在南京事件上的不作为责任,也即单凭第55条罪状,就被量以极刑,可见法庭对南京暴行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
不过需要说明,对日军侵华的普通战争罪审理更多地集中在与东京审判差不多同时期的十个国内B、C级法庭上,所追究的个人多为直接与中国军民发生接触的日本前线官兵或是宪兵,与东京审判着意追究国家领导人责任的出发点有所区别。
1948年11月4日,结审半年多的东京审判进入到最后的宣判阶段。25名被告中有7名被判处绞刑,16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另一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判决书依次宣读,过程直至11月12日。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此闭庭。死刑被告于次月23日执行,其余被告则服刑于东京巢鸭监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足以促使人们尝试使用司法手段规制甚至阻止战争。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审判向世人表明:可以向个人追究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法律责任。
如今“二战”和审判都早已结束,远远没有结束的则是关于战争和审判性质的种种争议。我们愤慨和诧异于日本为何迟迟不能对战争责任进行自省。而历史学者所能做的,是再次检视那些被法庭接受或驳回的证据文件,让事实再度回归公众视野。
注释:
[1]关于美国在战犯问题上的争论,见[日]日暮吉延著,翟新译《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和规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8—97页。
[2]“Report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Subcommittee for the Far East”(September 12, 1945), in FRUS, 1945, vol. 6, PP926—936.
[3]关于“ABC”级战犯(或甲乙丙级战犯)的称呼源于最初由美国起草的对日审判方案,其第一章的“A”“B”“C”各项分别对“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反人道罪”三个罪名进行了定义。对于A项所示反和平罪行,便由此后的东京法庭进行审理。而对于“B”“C”项所示的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则由同盟国在亚洲各战地设立各自管辖的法庭审理。被称为A级战犯的人其主要罪责都与侵略战争相关。此外,纽伦堡审判的设立方案中没有提议区分被告的主要罪状,因此“A级战犯”或“甲级战犯”专指在东京审判中的被告。
[4]程兆奇:《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5]1944年12月5日《宋子文致顾维钧电》,见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联合国战罪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资料》(二),档案号:020/10117/0051/0211,台北“国史馆”藏。
[6]东京审判虽为A级法庭,主要审理反和平罪行,但同时也审理普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即所谓BC级罪行。实际上法庭对于战争罪的量刑相当严厉,最终被判死刑的七名被告均与重大战争暴行相关。
[7]Cassese, Gaeta, and Jones, eds., Rome Statute, vol. 1, PP428—429.
[8]Yuma Totani,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82.
[9]1946年5月14日向哲在东京法庭上的陈词,Transcripts of IMTFE,Vol. 1, PP272—277。
[10][11]张效林节译,向隆万、徐小冰等补校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第584页。
[12]Transcripts of IMTFE,Vol. 6, P12861.
[13]Transcripts of IMTFE,Vol. 1, P3935.
[14]即中日甲午战争。
[15]菅原『东京裁判の正体』,第143—144页。
[16]川『东京裁判を裁く』下卷,第114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