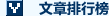忆我与曾彦修先生的交往
程中原
20世纪80年代,我在偏僻的苏北小城,曾彦修同志在首都北京,本没有一点儿交集。把我们联系起来、并最终成为忘年交的是张闻天。1976年,淮阴师专以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的名义复校,我在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承担了创办学报的重任。我了解到张闻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有作为但鲜为人知,加之他在我家乡去世,我深为同情,遂确定把“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作为我的研究课题。我心存一种期望,做好这个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后,学报上可以发表一两篇有些特色的文章。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在《淮阴师专学报》上发表的评介张闻天早年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文章,引起了当时正参与编辑《张闻天文选》的曾彦修等同志的注意。他们向刘英同志和邓力群同志作了汇报,邀我参加编辑张闻天选集、传记的工作。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定期到北京参加张闻天选集的编辑工作。这样,我认识了曾彦修同志,并在他和其他老同志指导下工作和学习。由此,我的人生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初识曾公
约在1981年的秋天,我利用国庆假期,到北京参加《张闻天选集》的编辑工作。起初,书名为《张闻天文集》。当时,文集编辑工作小组在人民出版社四楼的一间房间办公。说来正巧,隔壁就是戴文葆先生。戴先生是江苏阜宁人,他的夫人同我的二姐是无锡竞志女中的同学。我去的时候,戴先生正同彦修同志一起为人民出版社编辑一套四卷本的《鲁迅选集》。我对鲁迅也有一些研究,在淮阴主编过一本《鲁迅杂文选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他们是怎样编选鲁迅作品的呢?我不能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
进到戴先生的办公室,只见他和曾公面对面坐,正在讨论《鲁迅选集》第三、四卷杂文的选目。两张办公桌上铺满了卡片。鲁迅的每一篇杂文都有一张,卡片上写有该文题旨及是否入选的理由。经过商量,把不拟入选的摆到一边,把入选的留下。原来,为了编辑这本鲁迅杂文选集,他们对鲁迅十六部杂文集逐篇都作了研究,做了卡片,写下了是否入选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再商量决定。
他们问我那本杂文选讲是怎么编的,意思是向我取经。我感到很惭愧,在他们面前,那本书有些“不值一提”。我回答道:“我们那本《鲁迅杂文选讲》是给中学语文教师函授学习用的,选目三分之二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杂文,另外三分之一选了代表鲁迅杂文各种风格的名篇,以便让学员对鲁迅杂文的全貌有个初步的、具体一点的认识。”他们鼓励我说,这也是一种编法,好处是实用、针对性强,可以解决教学的需要。
《张闻天选集》的选编,邓力群与曾彦修等同志商定了三条入选标准:一是该文观点是张闻天首次提出的,跟着别人说的,说得再好也不要;二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错误的不要,因为这是一本公众读物,不是供进行学术研究的文集;三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过影响的,或虽然没有产生影响、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其思想观点处于前列的。按照这三条标准,一些在党内以至社会上流传的名篇,没有费多大劲就选定下来了。要花力气的是还有一些重要篇章,如重要会议上的发言、讲话,起草的重要文件,草拟的重要电报,大多并未公开,鲜为人知,需要搜集、查找、发掘。也就是说,必须在掌握张闻天全部作品的基础上才能编辑出比较真实可靠的张闻天选集。
除了编辑指导思想高明外,这个编辑组的组织形式也很有特色。邓力群(《红旗》杂志原来的副总编辑)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的成员有曾彦修,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何方,时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以前在张闻天身边,曾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达深,时任社科院西欧研究所所长,曾任安东市委书记,驻苏联使馆参赞;马洪,时任社科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茂仪,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主要参与领导小组工作的是曾、何、徐三位。再就是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萧扬,工作小组的组长,时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他从驻苏联使馆到外交部,就在张闻天身边,政治水平高,文字能力强,我帮他打下手,向他学习;参加工作小组做具体工作的,还有张培森、施松寒,他们都是党史专业,科班出身。能参加此项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指导考证“歌特”是谁
经过调查、访问、查档、发掘,陆续发现了不少张闻天的重要文稿,特别是遵义会议前的好文章。
我们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1932年4月出版的第1卷第4、5期合刊)上发现了署名“刘梦云”的长篇论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此文论证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理论上和方法上批判了“动力”派任曙、严灵峰的谬论,有力地支持了“新思潮”派,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取消”派论战胜利的基础。彦修同志指导张培森等同志通过深入研究,并采访王学文等当事人,确定刘梦云为张闻天的化名。
我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上,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其中《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是直接批评“左”倾错误的。“歌特”是谁?一时难有答案。我写了三四百字,从几个方面说明“歌特”很可能是张闻天。彦修同志说,这还不够。这两篇文章对于认识张闻天从“左”倾到反“左”倾的转变,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还是要用“乾嘉学派”(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该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的方法来考证。要“铁板钉钉子”,才能把文章选到选集里面去。于是发信请教,从陈云、杨尚昆、夏衍,问到差不多所有健在的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是,彦修同志指导我们进一步从各方面进行论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概括出了“个人惯用语”这一“试纸”。从张闻天1932年写的54篇文章中,概括出了他个人独有的惯用语。如:不用“虽然”而用“虽是”,不用“如果”而用“如若”,不说“直到现在”而说“一直到现在”,不用“和”而用“与”,不说“表现”而说“表示”等。这些“个人惯用语”,均一点儿不差地存在于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中。我写了一篇《“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考定《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为张闻天所作。张培森同志还下很大功夫,用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去检验瞿秋白等一切疑有可能为“歌特”的人的文章,所有这些人的文章都没有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考证达到了彦修同志提出的“铁板钉钉子”的要求。发送出去征求意见,得到领导和专家的肯定。后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
这些文章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了张闻天在犯“左”倾错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反对“左”倾的转变。彦修同志很高兴,专门写了关于张闻天反对党八股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评介文章,在《文献与研究》上发表。邓力群同志也很高兴,把《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第三节)、《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收进了《张闻天选集》,从而改变了最初想把《遵义会议决议》作为《张闻天选集》开卷篇的打算。
编辑、出版《回忆张闻天》
为了纪念张闻天,也是为撰写《张闻天传》搜集资料,在编选《张闻天选集》的同时,彦修同志指导我们编辑了两本书,一本是供内部使用的资料《张闻天自述》,把张闻天在各种情况下谈自己生平、思想的材料,按时间顺序编纂起来;另一本是供公开发表的熟人对张闻天的回忆录。我们访问了各个时期同张闻天有交往的老人。有的约请他们自己撰写,有的我们代为记录整理。正式出版的《回忆张闻天》一书是由彦修同志经手完成的。我随他一起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交稿,协助他做点儿事。一路随行,领略到他出版家的风采。
1985年8月30日是张闻天85周年诞辰。《回忆张闻天》一书要赶在此前出版。到7月中旬我们到长沙送稿时,还缺一篇最重要的稿子:杨尚昆的回忆文章。当时杨尚昆主席正忙于处理裁军一百万的大事,又不幸遇到夫人李伯钊病危。怎么办呢?彦修同志说:“等!等待杨尚昆同志定稿签发。”因为尚昆同志是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们一路回国,一起负责宣传工作,长征途中一道参加遵义会议。杨尚昆的四哥杨公是张闻天早年在重庆从事新文化运动时的战友,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张闻天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杨尚昆对张闻天的回忆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彦修同志遂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商定,在《回忆张闻天》一书第一篇预留12个页码。其他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其他文章从第13页开始排校完毕,封面用纸、插图用纸、内文用纸都从纸库调到印刷厂备用,都预先做好。尚昆同志的文章最终在8月24日定稿,赶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忆张闻天》一书也赶上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时出版。《回忆张闻天》的书名由邓小平同志题签,陈云、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为此书题词。
在这趟送稿期间,朱正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陪我们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看过韶山毛主席故居、毛主席纪念馆、毛家祠堂等之后,第二天,还去看了滴水洞。参观结束,管理干部请北京来客留言题词。这当然难不住彦修同志,他提起笔来,稍加思索,写下一行遒劲的大字:学习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我和朱正两个人附笔签名。
指导《张闻天传》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我接受了编写《张闻天传》的任务。按照原来约定,《张闻天传》要在1990年8月30日张闻天90周年诞辰时出版,事实上有难度,加上我1989年秋大病一场,预定的计划眼见无法完成。于是,想出了一个应急的补救办法:把已经写出的部分传记,同我先前发表的一些论文,按张闻天的生平经历编到一起,应纪念张闻天90周年诞辰之需。这样,在河海大学领导及其出版社的支持下,就出版了《张闻天论稿》。
这本书固然解决了一时之需,但离正式的传记毕竟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后又经过近四年的劳作,在领导的指导和全组同仁的支持下,到1992年暮春我才完成全书的初稿。上报以后,首先由彦修同志、何方同志审阅,指导修改。他们审定以后再报力群同志定稿。
第一位同我详谈修改意见的是彦修同志。他当时已经年逾古稀,我也还处在病后恢复阶段。1992年春末夏初,我们一起在无锡苍鹰渚的江苏省太湖干部疗养院修改书稿。
全书二十多章,一章一章修改。每天上午,彦修同志谈意见并商讨,有的段落他亲自写了稿子。下午和晚上,我就修改,修改稿随时交他审阅。一天一章,连续搞了个把月。
彦修同志是“一二·九”时期投身中国革命的先进青年,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他和宋平、邓力群等是同班同学,没有结业就被张闻天留校了。以后他又随张闻天参加了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在改稿过程中,他讲了不少马列学院的教学情况和农村调查的情况,丰富了《张闻天传》的内容。特别是关于1942年7月1日晚张闻天在杨家沟打麦场上同调查团全体成员和驻在该村的晋西北后方机关干部谈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伟大作用,生动深刻,十分感人。
他对张闻天活动的时代风云有切身体验,而我在传记初稿中写重大事件的时代背景往往不得要领。有的段落彦修同志干脆就执笔重写。例如:关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时的形势那一段,就是彦修同志重写的。他写道:
1935年秋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1935年夏季,日本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5月,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要求中国政府铲除华北抗日行动,撤退军队和国民党军政机关。6、7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照此办理,实际上将非武装区从冀东各县扩大到了整个河北省。6月底,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又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按照这两个卖国协定,国民党嫡系力量基本上退出了河北、察哈尔两省。1935年9月,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又发表声明,鼓吹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联合自治”。10月,日本内阁又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图谋将整个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汉奸殷汝耕在北平城东40里的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日本操纵的一片敌伪统治区。接着,日本又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妄图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名义上仍归南京政府管辖,实际上就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翻版。华北主权断送,中国形势危如累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他的修改意见,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点是对人物的评价要恰如其分。传记初稿对张闻天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高度评价。按照彦修同志的要求写了一段符合他当时所达到的水准的话,使评价比较客观公允:
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活动,展露了他日后成为革命理论家的才华。诚然,他这时所发表的许多见解,有些是对各种思潮所作的学理上的选择,有些是对现实生活的直觉中得到的朴素认识,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而形成稳定的思想体系,所以,在他此后的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免会出现反复与摇摆。这是完全正常的。这并不妨碍作出这样的估价:在五四运动当时,以思想、政治方面的成绩而言,张闻天是全国最先进的青年学生中的一个。
对《遵义会议决议》,彦修同志指导我们在充分肯定其伟大意义的同时,加上一段话:“我们当然不应回避《决议》存在着‘转变’时期或尚未完全觉察、或难免需要保存的旧的痕迹,毋庸讳言,这同时也反映着《决议》起草人张闻天的‘转变’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并具体列举了四条“旧的痕迹”,表现了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
另一点是十分注重语言的朴素。他好几次表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写得花里胡哨的。他多次教导我,张闻天是个很朴实的人,传记叙述他的言行要同他为人的风格一致,朴素而生动。
最后的一面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受朋友之托向彦修同志请教解放战争期间在山东渤海区进行土改时的一张照片,上面有曾彦修、田家英和毛岸英等人。朋友要曾老谈其中一位同志的情况。那天彦修同志精神不错,回忆了在山东的往事,谈了毛岸英学习的情况,只是要询问的那位同志,彦修同志带着歉意说,记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了,估计是地方上的同志,不是延安一起去的,延安一起下去的同志,大家都熟悉。
请教完问题以后,彦修同志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老程,张闻天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的作用,你还要写文章。”并鼓励我说:“你能够写好这篇文章!”这是继杨尚昆同志交代对张闻天还要拨乱反正、耿飚同志告诫对张闻天还讲得不够后,又一位当面交代我任务、对我寄予厚望的人。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几个月,彦修同志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他的嘱咐成为他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任务。
可以告慰彦修同志的是,我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约,已经写成了一部《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此书于201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八十周年纪念之际出版。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在此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20世纪30年代末,张闻天曾把一副自勉的对联书赠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身正何愁月影斜。彦修同志一直把它作为座右铭,以一生的行动践行了这句话。■
(责任编辑 王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