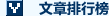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
张军锋
长期以来,围绕中共建党的诸多史实问题,如中共一大开幕闭幕日期、代表资格与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共成立的关系、建党文献中文原件的下落等都有过很大的争论,有些问题至今依然争议不断。其实,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受俄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多渠道开展工作的影响,各地建立起多个中国的“共产党”组织。而当下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日益深入,有专家指出,目前已经很难考证清楚继俄国革命之后,在中国自发涌现出来的“共产党”组织究竟有多少家了,但已经找到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至少也有五六家之多。对这些早期部分“共产党”组织进行一些考察,有助于我们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和运动初期的复杂状况有所了解。这将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波澜壮阔、泥沙俱下的真实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经过大浪淘沙脱颖而出的历史过程。
刘绍周、刘谦和俄国共产华员局里的
“中国共产党”
1919年3月2日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灯火通明。
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的30多个国家的54名代表在这里隆重集会。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也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但是,在与会的54名代表中,却有两位中国人。他们一个叫刘绍周,一个叫张永奎,他们是“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代表。
刘绍周(1892—1970),后改名刘泽荣,广东高要县人。五岁时随父亲到高加索巴统。1909年在巴统中学毕业后,入彼得堡综合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毕业后于1914至1916年间在高加索吉斯洛沃得斯克中学任数学教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俄国谋生的华工有近6万名,至十月革命前,在俄的华工已有30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为俄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遭到沙皇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华工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多个分布于彼得格勒、莫斯科、叶卡捷琳堡等地的小规模的旅俄华人团体。1917年4月1日,刘绍周等人联合各组织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刘绍周任会长,张永奎任秘书。
1918年12月15日,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情况,中华旅俄联合会联合了其他一些华工组织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其任务改为“组织华人劳动者与俄国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反革命和反对外国干涉者的革命斗争”。刘绍周任联合会执委会主席。
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旅俄华工联合会的重视不是偶然的,这与中俄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革命联系和战斗友谊有关,更与列宁长期以来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爆发后,旅俄华工中的先进分子英勇地参加了夺取冬宫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十月革命的艰苦岁月里,有70多名华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担任列宁的卫士,来自沈阳的中国工人李富清担任列宁卫队的组长。1918年初,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李富清等人又跟随列宁一道前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继续担任警卫工作。
1918年3月,俄共(布)中央根据列宁的指示成立了几个外国共产党小组。同年5月,这些小组联合为统一的组织—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直属外国共产党组织中央局。该局在苏俄举办了各国宣传员训练班,为各国培养建党的骨干。
1918年12月,列宁指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外国共产党组织中央局成立中国分部,专门负责华工的工作。这时,旅俄华工已组成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其中建立了由俄共(布)领导的旅俄华人共产党支部。由于列宁的重视和华人共产党支部的发动,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苏俄各地发展很快,华工共产党员也逐渐增多。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刘绍周和张永奎应邀出席并受到列宁的接见。此后,俄共(布)所属华人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
1920年6月18日,第三次全俄华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与会代表选举产生了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俄国共产华员局,统一的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正式形成。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中国组织无产阶级,实行社会革命,中央组织局“将来须移至中国”。出席这次会议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负责人沃兹涅先斯基,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就从苏俄给中国上海《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写文章,宣称要把旅俄华工联合会这个最初具有商业性质的协会变成政治组织,并称之为“新同盟会”,并说要把这个总机关设于俄国的“新同盟会”的活动扩展到中国。很明显,俄共成立俄国共产华员局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使它不断扩大和正规,然后移至中国。
这年8月,俄国共产华员局的机关刊物《震东报》第一期在莫斯科出版,在这期刊物的醒目位置印刷着该刊创办者的名称:莫斯科共产党总筹办处。
1920年11月,俄国共产华员局负责人、一直担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职务的刘绍周由于火车事故受伤,携眷随北洋政府派往苏俄考察军事、外交的张斯麂代表团回国。可惜的是,这位三次见到列宁、被俄共寄予厚望的俄国共产华员局负责人,回国之后,竟然很快与俄国共产华员局失去联系。[1]
接替刘绍周担任俄国共产华员局主席的是安恩学。他担任华员局负责人之后,加快了推进建立国内党组织的步伐。为培养中国革命急需的干部,共产华员局决定开设“中央党校”(直属华员局)和“教育培训班”(华人党组织地方分部主办),讲授国语、外语、共产主义史、宣传员实践等课。优秀党员要入党校或培训班学习。据北洋政府档案,培训班的学员“皆系投入俄营当兵之人……六个月速成毕业,分往中国,专事传布社会主义”。除了华员局机关报《震东报》之外,华人党组织和华工联合会还创办了《大同报》(华工联合会机关报)、《华工报》、《共产主义之星报》等多种中文报纸,并将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其他一些革命书籍译成了中文,在华工中大量散发;还组织各种形式的演讲会、报告会、讨论会,在华工中掀起了研讨中国革命问题的热潮。
为了就近发动中国革命,俄国共产华员局在1920年秋把机关从莫斯科迁移到赤塔。在众多俄国共产华员局党员中,对接触中国内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特别积极而且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作刘谦的党员。
刘谦的身世、经历和职务,至今仍是一个谜,我们只知道他的俄国名字是费奥德罗夫,他在党内的组织关系隶属于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所在地是与中国黑河隔阿穆尔河相望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这里居住着许多中国移民,州委员会的中国支部发行中文旬刊《共产主义之星》。
1920年7月28日,刘谦就索性使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正式名称给中国共产主义者写信,询问江(亢虎)的下落,希望中国同胞把江当成亲密的同志。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姚作宾……也参加了刘谦那个“中国共产党”。[2]
这段不足百字的文字给我们透露出很多重大的信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俄国就有人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这说明此时在俄国已经存在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更令人奇怪的是,后来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但随后又被取消代表资格的江亢虎和姚作宾竟然都是这个在俄国发号施令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竟然隶属于俄国共产华员局!
就在刘谦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写信的这个夏天,他还来到了中国,并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我们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中,见到了刘谦回到苏俄后于10月5日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写给阿穆尔州委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刘谦报告了与孙中山会谈的结果,同时提出了一份大胆的进攻中国内地的计划:
(1)立即把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以便能够密切配合为反对北方的反动政府准备条件;(2)为此必须在远东地区设立一个领导中心,拟把布拉戈维申斯克作为这个中心,将从这里向南方和在苏俄的组织下达指示;(3)拟把新疆省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中地点。驻扎在俄罗斯中部的中国军队已同南方首领孙逸仙举行了军队合并的谈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动。为了同孙逸仙保持密切联系;孙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就到这里来。[3]
刘谦的这份与孙中山达成的从西北进攻中国内地的军事计划,显得过于大胆而惊人,但恐怕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此时的孙中山的确正醉心于依托苏俄的“西北军事计划”。此外,有证据表明,黄介民和姚作宾的确与刘谦建立了联系,刘谦似乎有意以旅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核心,进一步联合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江亢虎和全国学联领导人姚作宾,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屡屡以“中国共产党”名义进行联络的原因。
对刘谦要把成立于俄国的中国共产党移植到中国去的构想,俄共远东州委似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远东州委所属的俄国共产华员局在1920年12月6日的会议上讨论了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必要性和联络上海、天津的青年组织的事宜,并“批准刘同志(费奥德罗夫)立即到中国出差三个月”;1921年1月16日又计划向中国派宣传活动人员,以在孙中山控制下的地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然而,这一切计划都因为一个无法预料的变故而胎死腹中。
雄心勃勃的刘谦带着到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前往中国,但他在通过中俄边境时突然被人杀害!时间大概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被何人所杀以及遇害原因至今不明。
这场变故,使俄国共产华员局的计划戛然而止,遭遇了巨大挫折。
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这些漫无计划的对华工作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些陆续派往中国的俄国共产华员局成员“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
1920年初以前,共产国际与中国国内的革命者尚未建立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苏俄还在进行国内战争,特别是俄国远东部分西伯利亚地区,仍处在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干涉军以及白俄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匪帮的统治下,加之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封锁了中俄边界,关闭了中俄交通。直到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初,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美、日干涉军之间发生矛盾,高尔察克被擒,美、英、日纷纷撤兵,西伯利亚的形势急转直下,曾加入武装干涉的亲日的段祺瑞政府封锁边界的政策也随之破产。
随着中俄边境交通障碍被打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直接联系的条件基本成熟。1920年初,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位“使者”,这就是帮助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随着维经斯基在中国建立的远东书记处和上海革命局卓有成效的工作,共产国际认识到,当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陈独秀和他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于是逐渐改变了依靠俄国共产华员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计划。
1921年下半年,俄国共产华员局逐渐停止了工作。以它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设想,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大潮奋起之前的一朵逐渐被人遗忘的浪花。
共产国际档案和江亢虎游记中
出现多个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1年夏天,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先后在莫斯科隆重举行。中共党员张太雷和俞秀松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这两个盛会。他们被会场热烈的气氛所感染、激动,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却也让他们心中有一丝忧虑。因为到大会报到之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唯一的代表,还有两个号称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代表也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个是姚作宾,一个是江亢虎。
江亢虎,就是辛亥革命期间曾经名噪一时的中国社会党党魁。1913年中国社会党在袁世凯威胁下被迫解散之后,江亢虎亡命海外,在美国侨居七年,一直到1920年9月回国,并筹备赴俄国考察。江亢虎赴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在苏俄政府的帮助下,收复中国外蒙古,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由于他的俄国之行得到大总统徐世昌和孙中山的支持,因此也受到苏俄政府和列宁的重视。江亢虎在俄期间,得到苏俄政府的“国宾待遇”,后者在生活、住房、交通及参观访问等方面都提供了最大的方便,而且他受到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接见。
江亢虎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正是共产国际“三大”开幕的日子,作为苏俄的“国宾”,江亢虎堂而皇之地以中国“左派社会主义党”的名义出席了会议,并且得到了发言权。但在会议的第四天,江亢虎的代表资格又奇怪地被取消。江亢虎为此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表示抗议:
第三次大会开幕当天,我领到了具有议决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四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Kabasky)同志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4]
关于这次收缴代表证的经过,江亢虎后来又有详细的回忆:
(我)本以社会党代表名义出席第三国际会,已就绪矣。闻某团代表张某(张太雷)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系由东方管理部(远东书记处)部长舒氏(舒米亚茨基)所介绍而来者,因往访之。……不意相晤之下,张闪烁其词,不自承为代表。余方异之,及出席时,见张与舒氏在座,因询之日:“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转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出席二、三日,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至终事后细访其故,始知张某等竟设为种种证据,致书于国际会,以中政府侦探目余。[5]
显然,江亢虎之所以被取消会议代表资格,是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抗议的结果。在这封信中,张太雷称江亢虎是“反动的北京政府大总统的私人顾问”“十足的政客”,并强烈抗议共产国际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
据《江亢虎新俄游记》中《纪中国五共产党事》的一节记载,1921年竟有五个自称为中国正统的“共产党”组织来到莫斯科,除张太雷、俞秀松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外,其余四个分别是:姚作宾代表的“东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生成立的“少年共产党”;黑龙江省黑河的原中国社会党支部“龚君、于君”改组的“中国共产党”;只身赴俄的杭州的“张君(张民权)”自称代表的“支那共产党”。其中以“少年共产党”人数最多。[6]
对于以上记载,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查证追究这些都标榜正统的“共产党”组织的详细情况,但这个现象已经足以说明当时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多种存在。仅从它们纷纷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情形看,它们可能都与共产国际多多少少有一定的联系。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也的确是由于俄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多渠道开展工作造成的。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者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而中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团体又缺乏相互联络,结果形成了多头联络,山头林立、错综复杂的现象。
多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一起在莫斯科出现,毫无疑问对还没有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立牢固的关系,并在共产国际开展工作,都是一种极大的干扰。因此张太雷和俞秀松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展开了斗争,并向共产国际提出抗议。俞秀松在1921年9月2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递交的声明中这样说:
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公民姚作宾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一起讨论甚至决定的东西(根据姚作宾的建议,共产国际拨给款项等),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因为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7]
共产国际认真对待了这个问题,在取消了江亢虎的代表资格之后,也中断了与姚作宾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联系。
黄介民、姚作宾的大同党
及其“共产党”组织
黄介民(1883—1956),原名黄觉,江西省清江人。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在江西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与陈溥贤、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的《民彝》杂志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成立了“主张四海同胞主义”的大同党,并与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有很广泛的交往。五四运动爆发后,黄介民以上海为中心参加了多方面的活动,还成了国民党系劳动团体“中华工业协会”的领导人物之一,成为上海学界、工界的头面人物,他创建的大同党也因此得以发展,号称吸收很多“印度人、朝鲜人、支那人、日本人等,合约三千人”。
后来一度担任中华全国学联主席的姚作宾也是大同党的活跃人物。
姚作宾(1891—1951),四川南充人,1918年自费到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姚作宾在东京留学生里面,已经是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当时,于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下属60余个分会,号称全国有50万学生受其领导,俨然形成一大势力。姚作宾作为日本留学生代表回国后成为全国学联的理事。
在维经斯基到中国之前,苏俄派遣各类使者来华的契机之一,就是出于对五四时期达到高潮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震撼和关心。而当时非常活跃的全国学联和大同党以及它们的负责人黄介民和姚作宾,自然也就成为苏俄使者感兴趣的对象。
为了与俄共组织建立关系,姚作宾曾于1920年5月代表全国学联秘密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共方面的文件称他为“同志”,说:
今年(1920年)5月,中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8]
由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了这样直接的联系,他和黄介民领导的大同党在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眼里自然就成为被共产国际“认可”的共产主义组织。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威连斯基在上海期间,似乎都与黄介民和姚作宾有过一些接触,但他们对大同党都颇为失望。他们在经过多方面比较之后最终认定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声望和号召力,他们代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更具建党基础。
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对大同党也评价不高。张国焘回忆说,他在上海与大同党人有过接触,回北京后向李大钊谈了情况,李大钊摇头说,他自己和陈独秀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黄介民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信仰和研究”。陈独秀则认为大同党的组建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和统一的思想,结果只能是“由毫无共同之点的人混合而成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大杂烩”。
随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各地建党活动的展开,大同党就日渐被共产国际冷落了。
1920年11月,共产国际另一位使者,“高丽人巴克京春”即朴镇淳,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朴镇淳生于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居俄国,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作为在俄外国革命者中最早受苏俄领导人信赖的骨干分子之一,他被列宁、斯大林委派为苏俄民族事务委员部朝鲜人民委员,并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和马林一起被选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
朴镇淳来到上海时,携带着大笔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其目的是巩固韩人社会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建立韩国临时政府与苏俄的联系;与此同时,他还试图促进、帮助经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对苏俄的进一步了解与接触,并在华组建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很明显,他的部分使命与在此前后来到中国的维经斯基和马林的使命几乎完全一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叠而互不衔接地派遣代表的混乱情况呢?我们只能说,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多渠道开展工作的必然结果。据石川祯浩考证,朴镇淳属于赤塔的俄共远东州委系统,其组织背景与维经斯基那条渠道稍有区别。
朴镇淳是否获知共产国际在他之前对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已经开展的工作,我们无从知晓,但他事实上在上海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展活动。他对中国并不熟悉,没有可靠渠道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因此只能通过旅沪的朝鲜革命者来联络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具有鲜明反帝意识,与朝鲜革命者关系密切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就自然地成了他接触的对象。
这样,在维经斯基离开中国,陈独秀南下广州,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由于经费困难而陷入窘境的时候,由黄介民、姚作宾领导的以大同党为基础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却在朴镇淳大笔经费的资助下在上海活跃起来。以至于在日租界警方看来,他们情报中获知的“支那共产党”“上海共产党”,都是指黄介民派的共产党,因而十分警惕朝鲜共产主义者与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接触和联合。
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在《施存统在警视厅供述概要》中得到印证。施存统在供述自己与上海社会主义团体关系时说:“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所创建,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界民(黄介民)派所组织,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而余有关者乃前者。”由此可见,黄介民一派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1921年5月,朴镇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代表近藤荣藏参加的共产国际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朝鲜共产党领导人李东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黄介民和姚作宾。
6月,姚作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朴镇淳、李东辉一起离开上海经欧洲赴莫斯科,出席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由于在科伦坡耽误了时间,他们到达莫斯科时已经是9月底或10月初。此时,不但共产国际的大会已经闭幕,张太雷和俞秀松这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已经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国际的正式使者马林主持之下,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已经闭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正式诞生。
而此时,作为姚作宾与共产国际桥梁人物的朴镇淳,也在朝鲜共产党的两派内讧中失去了信任,他在共产国际内执行委员的职务也由南满春代替。姚作宾在莫斯科勉强与共产国际举行了会谈,他在俄国人面前自称是共产党的代表,并吹嘘自己的组织拥有多少军队,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等人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抗议书。
姚作宾既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享有的声望,也没有足可依恃的强有力的组织,遭此打击,只好偃旗息鼓。
姚作宾、黄介民喧闹一时的“共产党”之所以昙花一现,就结束了其短暂的活动,固然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多渠道工作方式不无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的能力、声望不足以当此重任,何况他们的政治活动带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投机色彩。但俞秀松指责姚作宾为学生运动的叛徒,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姚作宾从俄国回来后,继续宣传宣传马克思主义。大革命时期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重庆从事工人运动。至于抗战时期堕落为汉奸,那是后话。
抗日战争时期,姚作宾分别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交通委员会组长、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社会局局长,1943年,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兼任伪新民会青岛总会会长。青岛解放后,青岛市人民法院在1951年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罪,判处姚作宾死刑。
黄介民后来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司法院”简任秘书、国大代表。建国初期,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江西省参事室、监察厅副厅长等职。1956年1月15日,在南昌去世。
注释:
[1]刘绍周回国后先是在中东铁路任职,1933年至1940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大任俄文教授,1940年6月任中国国民党政府驻苏参赞。1949年9月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外交部顾问,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70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
[2]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85页。
[3][7][8]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第44页,第45页。本书把刘谦译作“刘江”。
[4]《江亢虎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29日,莫斯科,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
[5]江亢虎:《新俄回想录》,军学编辑局1925年版,转引自(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6]《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页。■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 刘曾文)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