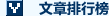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账本子”里的秘密
高明
1940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从前线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他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1]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山沟沟能出马列主义”的命题,但其中蕴含的问题非常明确,即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能力创造出适合中国的革命理论,其根系何在?事实上,创造适合中国的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不只是基本理论的探索,更重要而且根本的,是必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2]因此,1941年8月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特地指出,由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甚至不无严厉地批评道,有些同志“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3]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见一斑。为此,中共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
从1941年下半年起,按照中央部署,张闻天、高岗和李卓然等中共高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到陕北各地进行调查。其中张闻天等人组成的“延安农村调查团”的成果最为显著,产生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1942年7月27日)和《米脂杨家沟调查》(1942年11月19日)等报告,高岗带领的“西北考察团”的报告是《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1942年),李卓然等人写了《固临调查》(1942年3月)。[4]《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这一主题贯穿于张闻天、高岗等人的调查当中,不过,在《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和《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对地主经济的详细考察,前者甚至明确表示,“除调查这个村庄的一般情况外,主要力量集中在一个典型地主的调查上”[5]。
张闻天、高岗等人在调查中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地主经济,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张闻天明确提出,调查研究既“要把农村的阶级关系搞清楚”,又要着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为过去的调查“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6]因而,调查团主要集中于农村的经济状况。其次,这和他们调查的绥德、米脂的阶级构成有关。美国学者纪保宁(PaulineKeating)提出“延属的乡村重建是通过移民安置项目,而绥德的社会重建是通过阶级斗争”,具体的情况是,“许多绥德农村由地主阶级主导,这些人与城市政治精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7]高岗等人的调查也指出,绥德、米脂是大地主的聚集地。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绥德、米脂地主,尤其大地主的经济资料较为齐备。据刘英回忆,调查团到杨家沟调查时,他们了解到“当地最大的地主马维新家保存着将近一百年来的各种账簿,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都记得清清楚楚”。张闻天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啊”![8]于光远是高岗“西北局调查团”的成员,他的回忆录也谈到,只有大地主家才有“账本子”,而且“他们家里的文书账册也比较齐全,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便利。我们向地主要来了原始的账本,进行各种统计和分析”。[9]无疑,大地主家的“账本子”为调查团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有了这些条件,张闻天、高岗等人的调查不但精细地描绘了绥德、米脂地主经济运行的生动情况,而且对这一群体的观察和分析,也极具历史的洞察力和深刻性。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以马家沟地主为主要对象,尤其将地主马维新当作考察的典型。调查指出,地主经济的基础是土地,地主主要通过买、典等方式获取土地,而马维新拥有土地1175.5垧[10],其发家史可以上溯到清朝。调查显示,马家“买进土地的时间,主要是在光绪十八年及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光绪十八年为大荒年,二十五年为半荒年,二十六年为大荒年,当时人民饥饿不堪,争着卖地、典地,地价便宜,每垧不到十串钱……在这个困难时期,农民究竟活命要紧,土地是次要的”。[11]可见,地主大量土地的积累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灾年、荒年往往是他们扩展土地的有利时机。事实上,在张闻天等人作调查的近十年前,也就是1933年,陈翰笙、唐文恺等学者就组织过农村调查,巧的是,在陕西调查的王寅生等人也到过绥德、米脂,且接触了马家地主。在马家沟附近的崖马沟,调查者发现地主土地的来源主要是:“(1)放债以地为抵押;(2)债户人未能还债,将地典入;(3)押地及典地后,均收买进来。”这是因为农民随时可能遭遇各种经济风险,一旦无法抵御,他们也就随时有可能失去土地,其后果就是崖马沟“居户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佃户,所种土地,几皆为杨家沟马姓所有,吉徵镇马盛德次之”。[12]这一状况直到张闻天等人调查时仍在延续,即杨家沟除了地主,其他的全都是农民,而且“大多数则是租种、伙种、安种地主土地的佃贫农。全村137户农民中,有94户佃农,即有69%的农民,是受地主剥削的佃农。”[13]不仅如此,地主获取土地不光针对穷人,对于败落地主的土地,哪怕是自己的本家,也照样想方设法兼并[14]。地主的土地大都是利用类似的时机和途径而得来的。
在围绕土地而建立的各种关系中,除了最核心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关系也是重要的一环。据经济史家李文治研究,从清代前期开始,“官绅地主的权势相对削弱,广大奴仆雇工和佃农或获得解放,或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庶民地主也有所发展”[15],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租佃双方的地位已经出现了逐渐平等的趋势。大致来说,这一论断是确当的,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农民如果失去土地,要么就变成游民,要么就沦为佃农,如此一来,大多无地或失地的农民就不得不和地主确立租佃关系。一旦确立租佃关系,双方事实上就处于两重关系中:一层是佃权关系,这一关系中地主仍占据优势。张闻天指出:“一般来说,地主将佃户租地全部或部分收回转租或者自种,是地主对付他所不满意的租户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他为了达到加租目的的一种手段。”[16]即便中共在抗战期间推行减租政策,也时常遭到地主的抵抗或规避[17];另一层是收交租关系,地主更是居于主导地位。高岗等的调查谈到:“绥、米农村习惯如逢荒年、歉年,农民可以缓交或少交地租,作为欠租,留待后来陆续偿还。但是旧欠未清,新欠又增,这样日积月累,几乎凡是老佃户没有一个不欠租子的。……有的欠租是三四辈积累下来的。”更可怕的是:“欠租对农民是一个重大负担,若遇收成稍好,农民一点余粮,地主即以欠租形式搜刮而去,使得农民永世不得翻身。若是问一个农民欠租多少,什九回答不出来,问他为什么不到财主家看看账,一个农民回答:‘财主家的账谁敢去看来!’农民对欠租问题态度是这样:只要地主不来讨就胡混下去,至于欠多少,自己不敢去问,也不愿去问。就是有农民去看账,地主说:‘你要还旧欠吗?’吓得农民也不敢看了。”[18]张闻天的调查中也发现,每个租户每年都有欠租,这种欠租世代相传,几辈子人都无法还清。而“欠租”形成的原因,“除了地主贪得无厌之外,还有天灾人祸等等原因(如遭受自然灾害,死了人,荒了地,或病了,庄稼务得不好等)。这种欠租,地主当然平时不取利息,但他却永远‘挂’在租账上,只要年成一好,地主即要追交欠租。所以农民在丰收之后的实交租额总要超过原租额,这就是地主们追交欠租的结果。但地主们并不以农民们还清欠租为满足。他们希望农民永远依附于他,希望在农民身上榨取无穷的脂膏。所以在这种丰年及交租额超过原租额的时期,地主就照例加租。这样,遇到荒年,佃户交不起租或者少交租,欠租就不断增加;遇到丰年,地主就迫着农民多交租,接着就是加租。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加租的周期性。所以农民不但永远还不清欠租,而且他们被地主剥削的程度则年年增加,直到地主抽回土地转租给别的佃户为止。但即使在地主抽回土地之后,欠租仍然挂在地主的借账上,年年逼佃户交还。……农民永远在地主的脚下翻不过身来”。[19]正由于这些原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农村问题,发现单凭减租根本难以奏效,有效的办法是减租的同时必须保障佃权,否则,地主随时有可能“扯佃”(收回租地或变更佃户),农民的处境仍然非常不利[20]。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共延安时期保障佃权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不仅是制止地主威胁农民反对减租的主要方法和发动农民敢于进行减租斗争的前提,而且是提高农民生产情绪,改良农作法和增加生产不能缺少的条件。”[21]
地主经济的另一主要来源是放账,即高利贷。张闻天的调查指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借到高利贷,想借贷必须要有抵押品。抵押品“有指地,指窑,指马,指骡,指牛,指树,指工,指青苗的不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为指地约。一切较大的‘揭’账(借账),没有土地的抵押,是不成的”。尤为严重的后果是,如果债务人典地借贷的话,“一年两年不能依约还本带利时,债务人即须‘撩地’,将所抵押的土地交给债权人耕种管业”。有些债务人刚开始还只是典地,但随着债务增加,最后却不得不将典地出卖。失去土地后,债务人有的“改变职业或脱离本乡”,但“多数从债主手里租种自己典出或卖出土地,尤其租种典地的更为普遍。这样,就由债务人变成了租佃户”。还有些债户,“虽是他们揭的款项是很小的。他们用工、用草、用西瓜、用猪肉、羊肉、用谷子、用豆子、用麦子,用一切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付利息,但结果仍然还不清”。[22]可以说,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罗网,债户几乎再也无法脱身。
绥德、米脂地主经济的基础是土地,但整个经济却是由“买地、典地、收租和放账”四项组成,而且,几者之间又相互转化,使得地主的经济和其他权力不断巩固。张闻天着重分析了马家的“崇德厚”[按:指马家创办的一个字号,主要从事放高利贷、典买土地(包括典窑典房)、出卖粮食、临时无利贷款和临时杂货买卖等],报告中揭示出地主经济的循环过程,即“‘崇德厚’的资本,就是粮食、典地、买地、行本银、借本银。它的营业就是从典买地收进租粮,把租粮卖出换钱,从行本银收进利息,利息又是钱,于是又把钱借出收息,或典买土地收租子。这样循环不已地流转下去,就使它的资本年年扩大,它的盈余年年增加,‘放账置地’的目的,也就可达到,至于无利借贷,虽无利息,但却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帮手”。[23]事实上,“买地、典地、收租和放账”等的相互转化,构成了中国地主经济运行的全过程。高岗等人的调查指出:“绥、米大地主的起家历史多与商业剥削、囤积粮食有关,如高庙山常家、刘家峁姜家,过去都在米脂、镇川、吉镇开生意,他们一部分土地来源是靠贩送囤积粮食,趁荒年大量掠夺农民土地。直到今天,绥德市——警备区的商业中心——的私人商业资本差不多都和地租有密切联系。如×××、×××、×××诸人都是大地主兼大商人。抗战以来,特别是减租条例颁行之后,地主更有从土地经营转入商业经营的趋势。”[24]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