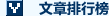我劳作故我在
柳鸣九
导语:柳鸣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他是第一个将20世纪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十多年前,他的《法国文学史》(三卷本)就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是中国文坛规模最大的多卷本别国文学史。2006年,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2018年11月19日,85岁高龄的柳鸣九先生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除了习惯摆弄自己的专业以外,还在闲暇之余写了不少随笔。阅读柳先生的随笔作品,会感到别具一番思想的魅力。
记得有位气吞江河的大人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思的话:书本是死的嘛,搬来搬去有什么了不起?这位先生说得没错。因为我们这些知识劳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搬运工,我就不止一次说过,我是桥上的搬运工,是中西文化交流桥上的搬运工。我们的作为不外是把外国的搬运到中国来,把过去时代的搬到当今时代。的确,把书本与知识搬来搬去,不可能有什么“大出息”,没法和搬挪山河、搬演历史相比,享用不到那两种“搬运”的莫大荣光,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还是回到现在的话题上来吧……
勤奋是对自己致学经历最基本、最具体、最确切的概括与总结
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蹲着看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一看就是大半个小时,我看到的蚂蚁都是急急忙忙,跑个不停,到处找吃的,从来没有见过一只在慢悠悠地闲庭信步,而它找到块头比较大的一点食物时,那股拼死拼活奋力搬运的劲头实在使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块头超过自己体积的食物,不多一会儿也被挪到好远的地方……难怪在人类的语言中有“蚂蚁啃骨头”之喻。蚂蚁虽小,虽微不足道,能把骨头啃下来,靠的就是它的执着与勤奋。
终于我发现了,如果要总结我的作为之所以然,首先,就应该把原因归结为我的勤奋,蚂蚁式的勤奋,我这样一个“矮个子”有所作为,正是“天道酬勤”的结果,这是如“蚂蚁啃骨头”一样合乎常理常情,是最颠扑不破的结论,也是在“文人相轻”的领城里、最不引人有争议的鉴定,最容易为世人所首肯、所认同的鉴定。时至今日,过了古稀之年,我倒觉得“勤奋”二字恰巧是对自己致学经历最基本、最具体、最确切的概括与总结,我深知,我在本院是一个历来都“有争议的人物",即使如此,即使是在社科院对人对事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有争议的现实环境里,这个评价也算是坚硬得颠扑不破,谁都认可的,就像算术中的最大公约数。
其实,勤奋是中国学子、中国学人的普遍共性,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特点,因为,说到底,中国人是勤劳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正常的中国学人而已,而且,勤奋度也只属于中等水平。我并非一个天生勤奋的人(当然也不是生来怠惰之人),我的勤劳度、勤奋度往往最初决定于生活的需要,如,到一个环境,为了自己生活得舒适,我总要打扫打扫卫生,布置环境,我从小也有每天整理房间、扫地、擦桌椅的习惯,但从来都无意于做到“明窗净几”的程度,仅仅满足于大体上过得去就得了,因此,常被我母亲评为“表面光”。我每面对一种境况,绝非勤劳成习,以自己动手为乐,而天生有点求轻松、喜安逸的倾向,能得闲时且偷闲,如:我平生不爱做饭洗衣等家务劳动,早从四十多岁起,就不惜支付稿费收入,雇人代劳家务,至今已完全解脱数十年。这一点我颇像我的母亲,她毕竟不是勤劳成性的农村妇女,而像小市民阶层的妇女那样,颇善于“享点小清福”,抗战相持阶段,父亲在桂林供职,收入稳定也还算充裕,我母亲在耒阳带着我们兄弟三人生活,她本人健康而能干,但家里就用了一个“老妈子”,对我这样的家庭而言,这是很罕见的……
我家是在惊涛骇浪的黑夜中漂泊的小船
我喜欢闲适而不紧张,安逸而不艰苦的性格,在我年龄偏小的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我的童年过得轻松懒散、四体不勤、好逸恶劳,没心没肺,近乎顽劣,既不美好,也不纯真,没有什么事值得怀念。但在我小学毕业到上中学这一段不长的时期里,我却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不懂事到懂事,从好逸恶劳到手脚勤快,从读书不用功到开始用功,整个人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似的。变化的契机是我一场大病。那时,我们家住在重庆,父亲没有工作,只靠打零工维持全家生活,过得很窘迫,几乎像衣食难保的城市贫民,这时,偏偏又碰上病灾降临,不知是怎么搞的,我得了盲肠炎,而由于家里人在医学卫生方面的愚味无知,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一直没有正式就医,拖了半个来月,等到正式医院一瞧,已经发展成了晚期腹膜炎。肚子里一个大肤包随时可溃破,已经不能开刀,时刻有生命危险,需要立即住院,绝对静卧,每四个小时打一针盘尼西林,权且将死马当活马来医。那时的盘尼西林刚发明出来上市,价钱极为昂贵,我父母亲变卖了他们少有的积蓄两个金戒指,才保证用上了此药。我经过三个星期的医治,总算转危为安,康复出院,但家里则往前又穷了一大步,而且,在这三个星期里,我父母亲备受煎熬,极为劳累,我住在离家十几里远的医院里,需有亲人全天陪护,我父亲白天不能离开病房,夜晚则把几张椅子拼在一起,权且当作床铺打打盹。我不仅需要绝对静卧,而且还需进高营养的纯粹流质,不能有任何渣滓,我母亲就每天在家熬牛肉西红柿汤,父亲则要走上十几里路,把牛肉汤送到医院给我喝。在这几个星期里,我从生死边界亲眼见证了家境的窘迫,生计的艰困,父母的愁苦与辛劳,我从一个没心没肺的少年,变得很有家庭忧患意识,很有多愁善感亲情,只要父亲稍迟一点回家,我便忧心忡忡……这时,在我心目中,这五口之家就像一只漂流在大海上的小船,周围是沉沉黑夜与惊涛骇浪……我对自己家庭境况有了清醒的认知,也就真正从心底悟出了我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作为长子该做些什么、该如何做。我开窍了,我懂事了,我知道了努力上进、勤奋读书才是我的正事,才是我面对父母、面对家庭的分内的职责……这是我上了路的开始。
中学奠定了我以勤奋始、以勤奋终的文化生涯
如果说,家庭生存的压力使得我开始懂事上路的话,那么,接着而来的中学教育以及大学教育的学习压力则使我在勤奋求学的路上走得更坚定、走得更用心。再后,工作岗位上持续了一辈子的业务压力、在士林中立足的压力,则使我勤奋的劲头从来不敢放松,至今,终将完成我以勤奋始、以勤奋终的文化生涯。我所上过的四个中学,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长沙的广益与省立一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名校,以相对悠久的历史、雄厚的教育资源、优秀的教育质量而著称,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师资水平高,二是生源质量好,也就是说学生的文化知识基础较好,很多都出自“书香门第”或知识阶层。这对我来说,首先就构成了学习成绩的压力与身边同学关系的压力,我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不可能有如鱼得水之感,不可能轻松自如,我必须比别人加倍勤奋努力才能待下去,由此,我才开始养成了“笨鸟先飞”“笨鸟多飞”的习性。与此同时,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性,那就是喜欢跟周围的同学比较,不是争强斗胜的“比”,我文化功底不及他们,谈不上争强斗胜,而是找差距的“比”、不怕痛的“比”,一比之下,自己的短处与弱项就一目了然了,由此自己在课内就努力追赶,在课外则进行恶补。我在中学期间恶补“准文言文”的写作、多背诵古文观止、勤练作文、恶补英文语法等等就是这么来的,我虽无语言天分,但“勤能补拙”,毕竟缩短了差距。当然有些方面,我再努力也收效甚微,如数、理、化,我毕竟不是那块料,始终是个低等生。另外,扩大课外的阅读面,也是我奋发图强的一部分,正是在初高中阶段,我读了相当多中国与外国的文学作品,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郭沫若、叶圣陶、丁玲、朱自清,以至张天翼、张资平等等这些作家的主要作品,尤以茅盾与郁达夫为多,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基础,就是在中学阶段打好的。至于外国文学,凡是能见到的所有中译本,我几乎都读过,书源一是从图书馆借阅,二是在书店的书架前“站读”,一站一读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我把过去的懒散贫玩改成了经常泡书店的习性。与我的找差距、努力赶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习惯于找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又引发出另一种习性,那就是喜欢对周围人进行观察,分析其长短、优劣、得失、成败,并重在善于发现他人身上的特点与优点,逐渐又发展为比较善于发现其内在积极因素与正能量原子,我自认为自己一辈子看人看事,尚不失宽厚,不失通情达理,其渊源由此而来,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眼睛不尖,过分天真迂腐。这种识人之道,于我生待人处世大有好处。甚至可以说,这种识人之道,对我认知我散文作品所描写过的那些人物至关重要,对研究与分析文学名著中那些重要人物形象,也不无助益。总之,我的中学时代在我一生中开了个好头,它给我带来了毕生的立身之本:勤奋努力,有了这个“本”,才谈得上有其他的“派生”,有其他的结果。
几十年来我过的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书斋生活
上了北大,有了明确的专业方向,更是十分自觉地勤奋用功,不仅要求自己把课内的专业学好,而且还在课外给自己加码,重重地加码,如像学了外文,早早地就在课外找了一本文学名著来进行翻译,我最早的一个译本《磨坊文札》就是这么来的;历史课老师只要求交写一般的读书报告,自己偏偏扩大规模成为一篇“准论文”;修了王瑶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就要求自己在一个学年之内把《鲁迅全集》当作课外读物全部读完,而且还逐篇做了主题摘要;闻家泗教授指导我写学年论文,论的是雨果的一部浪漫剧,我却又把浪漫派的文艺理论建树也扩充了进来,洋洋洒洒一写就近三万言……
那时在北大,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得很响,课程既多又重,自己又在课外如此重重加码,除了在自己平平资质所允许的范围里提高效率外,主要就是靠挤时间、拼时间、开夜车去完成了。如此下来,到了三年级,就爆发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每天晚上只能入睡一两个小时,而且还老作噩梦,种种噩梦中总有那么一个经常上演的“保留节目”,那便是梦见一个炸弹从天而降,掉进自己的脑壳,在那里面开花爆裂,噩梦机制是那么缺德,它让你不能动弹地躺在那里,慢慢地细腻地体验。炸弹在脑壳里爆炸的过程、巨响与能量……神经衰弱如此凶猛袭来,眼见就有辍学病休的危险,于是,自己就赶忙又“勤奋”地跑医院,扎针灸,煎中药……总算勤奋劲又不负我,我较快地摆托了神经衰弱的阴影,胜利地完成了学业。
一种行为方式成为一种惯性后,持续下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所以获得“勤奋”的这个“最大公约数”式的评价,不过是多年来凭惯性这样做下来了而已。概说起来,也很简单:几十年来,我基本上过的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书斋生活,从没有享受过一次公家所提供的到胜地去“休假”“疗养”的待遇,也很少到国内好地方去“半开会半旅游”,当然每天夜里12点钟以前就寝也是极少的。所谓“勤奋”,说到底,基本上就是一个“挤时间”的问题,尽可能地在学业上多投入一些时间。如果没有挤的自觉性,一个人每天的时间不过就是那么一些,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的那一个时期里,每个人所能有的时间总量还大大打了折扣:几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路线斗争、斗私批修、政治学习……把业务工作时间分割成了零星碎片,且不说“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就误了大家整整十年……如果,再不“只争朝夕”,自己所剩下的时间就很有限了。我远没有先贤“头悬梁、锥刺股”的那种苦读精神,只不过是不放松、不怠情,按平常的“勤奋”程度往前走而已,当然,为了多挤出一些时间,免不了就怠慢某些自己认为无意义的集体活动,如像游行集会、义务劳动、联欢郊游之类的,甚至溜会、称病不出这种不入流的事也干过不止一次两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引起了诸如“脱离群众”“重业务轻政治”之类的非议与侧目而视,当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来临时,还领受过一些大字报、大批判,诸如:“修正主义苗子”“走粉红色道路”(身上涂那么一点红色,骨子里实为白色,岂不就成了粉红色?)“严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等等。
如果说,我的确将“勤”视为治学之本,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学问勤中得”以及“业精于勤”之类的古训格言自幼就诵读牢记而后身体力行。我的文化底蕴没有这么厚。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这些格言我是很迟才读到的,以勤奋为治学之本,完全是我自已的存在状态所决定的。这一种主观精神与原则只不过是从主体存在中生发出来的结果。事情很简单,我出身于劳动者的家庭,父母费了很大的劲才使我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我不能不以“勤”来善待这些条件。而要争取将来能得到比我父母优越一点的生存状况,我也必须努力、勤勉。这便是最初的原动力。及至进入到了专业的领域,起作用的便是专业技能的压力与周围环境的压力了。
不加倍努力,就意味着放弃,就意味着出局
学海无涯,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如此。我所从事的学科是法国思想文化,在整个西学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与地位,在这里,有人类最为美好的社会理想:自由、平等、博爱,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有充满独特个性的艺术创造,对我来说,这种文化其高度真如喜马拉雅山,其浩瀚真如大洋大海,而且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与奇妙的引力,足以把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与精力都吸收进去,就像宇宙中的黑洞;足以使人在其中忘乎所以、流连忘返,就像童话中的幻境。这既是专业魅力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是对投入者贡献自我的要求与压力,因此,面对着这样一个如高山、如大海的学科专业,我以自己的中等资质实不敢稍有懈息,实不能不献出自己全部的精力与时间,不过,我同时也是很怀着热情与愉悦去献出自己的精力与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所收获、有所拓展进而得到了社会承认与公众赞赏的话,那其乐就更大矣!
我大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翰林院”这样一个最高的学术机构。在这里,比肩而立的翰林令我辈只有抬头仰望的份,本学术专业领域,早有钱钟书、朱光潜、李健吾、卞之琳、冯至等学术标杆高悬在头上。要攀登的学术阶梯更是使人见而发怵,我一进文学研究所,就眼见不止一个不无才能的青年研究人员已经在最低一级的学术阶梯(实习研究员、助教)待了七八年未动窝,面对这种形势,自己不加倍努力,就意味着放弃,就意味着出局。说实话,那个时期,“翰林院”的业务压力似乎比现在要大一些,当年,不无成绩、不无学养的中级研究人员因无代表性的著作而被炒出“翰林院”的屡见不鲜,而研究员没有出版过几本书的人则几乎就没有。这种压力当年鞭策着我辈青年埋头往前赶,这未免不是一件大好事,也可以说是一种“必先劳其筋骨”的磨炼吧!
从事精神生产的人,都乐于把自己视为体力劳动者,与工人、工匠无异,并无意于强调自己高人一等,巴尔扎克就曾把自己称为“苦役”,罗丹的《思想者》也不是一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文质彬彬的上等人,而是一个全身赤裸裸的“苦力”。他全身饥肉紧绷,拳头紧攒,显然在支付巨大的体能,如果说他与一般的体力劳动者有什么天然区别的话,那便是他从事的不是简单、重复、机械的劳动,而是要达到较大创造性的劳动,他必须关注自己产品的创造性、独特性、突破性。
学术研究就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
我很高兴自己的一生是不断劳作的一生,而不是“四体不勤”“不劳而食”的一生。作为一个劳作者,我自然也有所有“劳动者”的习性,除了要求自己有不断操作的勤劳外,也很要求自己的“所出”尽可能带有创造含量、独特含量、知性含量,因为我知道,我们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是面对着有头脑、有理性的人群,如果你对他们有起码的尊重,而不把他们视为任你哄骗、任你忽悠的小孩或白痴的话,你就必须殚思竭虑,绞尽脑汁,拿出真货色来,我不敢说,我这么做做好了,但我的确是要求自己这么做的:如,我努力追求学术研究就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这样的境界。我对自己有此要求,并非我有慧根悟出来的,只不过是听从何其芳的指导而已。其芳同志——他生前我们都这么称呼他,充满了爱戴与敬意——他是诗人,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老资格“文艺战士”,因此,成为文学研究所的创建者与第一任所长、党组书记。作为党政“双肩挑的第一把手”,每当政治运动、“路线学习”来临时,他总有责任做“动员报告”“运动总结”之类的讲话。说老实话,我一直觉得他身上存在着诗人、学者与“党员政治家”的矛盾,他在上述那些政治报告中总免不了要检讨自己的“重业务”“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也总免不了要谈些科研工作、学术工作的话题。在我看来,他的“政治报告”中最动听的恰巧就是这一部分,因为,这里有他自己的经验、真知灼见与自我体验,其中,“学术研究工作就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就是经常出现的一个题旨。在这个问题上,我倒的确称得上是他的弟子。我信从这一学理,当条件允许时,我也力求身体力行,予以实践,而且多少也做出了几件广为人知的“大事”:六十年代提“共鸣问题”大概可算是其一;最大的一件则要算是1978年对长期统治外国文学领域的“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进行系统的批判;此外,就是同一时期重新评价萨特及存在主义以及后来针对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左拉与自然主义进行重新评价等等。这些事之所尚可称为“大事”,是因为它们都有全国性的文化学术影响,并已经被时间与历史证明了它们是有道理的、起了积极作用的。
再如,在劳作中尽可能从难从重以求产品有扎实的劳动含量,切忌避重就轻,虚而不实。在学术文学界,一旦拥有一定地位后,就会有一些诸如搭顺风车署个名,借已有权位不劳而获、分一杯羹的“美事”,窃以为此类行为实非诚实劳动者所应为也,宜慎戒之,还应要求自己保持劳动者本色为是。我自己主持多卷本书系的编译工作时总要亲自动手,编选一卷或翻译出一卷作为“标本”,至少要提供出有新颖的编选视角、有思想闪光点且分量扎实的序言,作为其劳动品牌标志。至于具体的编辑工作,更是要亲力亲为,有时丛书达数十卷之多,其每一卷的序言皆出自我手。
对于为文作评,则力求有一点新意,有一点创意,尽可能去陈言避套话,虽然我们这一代人为时代社会条件所辖,几乎逃脱不了讲套话、重复官话的命运。在知性上则以自己有限的才力,尽可能师法钱钟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先贤典范,纵不能做到引经据典,穷历万卷书,妙语连珠,华章熠熠生辉,总也要达到“及格”水平: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议论行文时而也得有一两个亮点,一两处深度。我智力平平,天生无“才思敏捷”助我,这样做虽不说有“苦吟”之窘迫,劳作的艰辛还是很有一些的,但每得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文章,劳动之后的酣畅与愉悦就构成了一种乐趣,这是我生活中最珍视的一种乐趣。面对着那些署有自己名字的产品问世时,则因为其中无一不存有自己或多或少的思想观点、感受体验、思绪情愫、文笔文风、凝现着自己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与满足。
“我思故我在”“我劳作故我在”,这种存在方式、存在状态,带给了我两书柜的劳绩,也带给我简朴的生活习性、朴素的人生,甚至我的“生活享乐”与生活情趣也是再简单不过的。这么些年以来,我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一次高消费与高享受,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劳作(包括阅读与爬格子)、散步、听音乐、看电视、体育活动而已,虽然生活如此平淡,甚至在旁观者看来甚为清贫、寒碜、索然寡味,但我还能从其中体验出不少乐趣:为文作书,从无到有,言之有物,亦有亮点,首先就有劳作的乐趣、创造的乐趣。文章发了,书出了,拿了稿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其乐多矣,带小孙女去餐馆用稿费“撮一顿”,此一乐也;带着稿费去逛书店,随意购些喜欢的书,此二乐也;收到扣税单,再次确认自己作为纳税人对社会又作了一次“奉献”,此三乐也;如果文与书在社会上得到佳评,有好反应,则又是一乐也……小乐趣之所以多多,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切都是劳作的结果,这种劳作者的自豪与乐趣,这种简朴的平民乐趣,这种心安理得、毫无愧疚的乐趣,恐怕是躺在安乐椅上一支烟在手之际,就有种种“人账”“奉送”“名利”“回报”“献礼”纷至沓来的高级人士所体验不到的。
这种存在方式、存在状态同时也必然在我对人对事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倾向上打上深深的烙印,这里既有合情合理,也有不全面与偏颇;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浅显局限;既有社会公理,也有个人不平。加以我脾性直坦,又自信“靠劳动吃饭”,有恃无恐,忘乎所以之时,论人议事就不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如此只求自己痛快,棱角分明,必然引起矛盾与争议,给自己平添不少阻力与困顿,我的学术生涯并不顺利,与此不无关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己既是自我的打造者,也是自我的敌人……这正是我作为一个劳作者自我存在生态的两个方面。■
(责任编辑 樊燕)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邓园”往事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从被...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刘志丹在永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