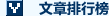国难当头始人生——回忆少年时光
许还山
1937年7月13日,七七事变后的第六天,我出生在北平东城十一条胡同东面一个叫白仓门的大宅院里。这座宅院是我外公的私人宅邸。段祺瑞执政期间,外公做过陆军部军务司长,后来又升到陆军部次长,还任过汉阳兵工厂厂长。然而,尽管当时外公家的显赫声名,也不能抵御或减轻日寇对外公家宅肆虐横行。
我的父亲许凌青当时因联名北平各大学教授抗日被捕,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饱受酷刑折磨,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并以外公的全部家业和老少人丁担保,方得出狱。父亲带着满腔愤懑、拖着布满血痕的幸存之躯回到家里,才第一次见到我这个已经出生三个月的儿子。
由于日寇侵华所导致的战乱浩劫,年幼的我难以得到足够的乳水,瘦得皮包骨头,满脸皱纹,活似一个小老头。母亲愁苦不堪,多次认定我活不了。父亲看着我这个虽生犹死的“老头儿”,悲愤之中,想到北宋岳飞面对强敌发出的千古誓言“还我河山”,将胞姐和我取名为还河、还山。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在国难当头之际开始的。
颠沛流离,
目睹侵华日军暴行
父亲1922年8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会成立大会,在“二七”大罢工惨案中险遭杀害。北伐期间,因为受到污蔑迫害,被开除党籍。但这之后他仍与中共董必武等同志保持密切联系,继续坚持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做党的外围情报工作。抗战期间,他又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各种身份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中共地下党的资助和掩护下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蛰居香港。半年后,母亲带着尚未学步的胞姐和襁褓中的我赶到香港与父亲会合。后来,日寇将战火推向东南亚,香港沦陷。在日寇进攻广州的炮火下,父亲携全家挤上了逃往广州的火车,继而辗转进入当时的陪都重庆。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重庆度过的。70多年来,每每提及重庆,我的心里都会泛起一种苦涩和悲凉。从1939年到1945年的六年多时间里,日寇对这座山城实行“无差别轰炸”,不管是军事要地、政府机构还是平民百姓,一概狂轰滥炸,以逼迫中国投降。
我们家住在重庆东水门里的东正街二十七号,这是一座陈旧的木结构杂居楼。1943年前后,这座木楼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空袭警报。每天黄昏时分,全楼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匆匆做饭、吃饭、刷碗,收拾好衣服细软,谁也不敢大声说话,竖起耳朵凝听着空中随时会响起的警报汽笛声,撩起窗户上厚厚的遮光窗帘一角,瞭望江边方向那座高高的木塔上是否升起了预报敌机来袭的红色球灯—第一次升起一个红球灯是空袭警报,需要马上锁门,尽快向防空洞转移;升起两个红球灯是紧急警报,说明日寇的轰炸机已临近重庆;第二次升起一个红球灯的时候,意味着警报解除。“跑防空洞”是当时重庆人每日的“必修课”。
警报天天都有。我记得那时候总看到无数的民工,整天都在沿江的坚硬岩石上开凿、爆破,打造一个个防空洞。有一天,听父亲说,不知是哪个防空洞里,躲警报的老百姓被关在里面窒息而死,成了当时的一大惨案。我们全家在长期、频繁的大轰炸中得以幸存,无一伤亡,实属万幸。
日寇投降以前,父亲一直在重庆工作,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就职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并兼任陆军大学政治总教官,少将军衔(实际是在中共西南局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
1945年8月的一天,屋后的小街上人声喧闹:“鬼子投降啦!鬼子投降啦!”正在病中的母亲立刻翻身下床,拉着我和姐姐,抱着五妹,穿过黑黑的过道,冲到街上。街上挤满了人,男人们几乎都赤膊,汗流浃背地在烈日下伸长脖颈,拼命呼喊:“真的吗?投降啦?好呀!”“鬼子狂到头啦!”
那天晚上,天刚黑,母亲锁上大门,抱着、拉着、轰着我们五姐弟,和镇上的人们一起挤到正街上看烟火。这次看到的烟花,是我长大以后在各地所看到过的那么多瑰奇亮丽的高级烟花所无法比拟的。
迁居南京,
父亲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抗战结束了,我们一家和当时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一样,都盼望着过上安定祥和、不用再奔波逃难的日子。当时我和姊妹们都太小,远远不是父母商讨抗日胜利后何去何从的对象。母亲说,父亲要把家搬到延安去,并且再三嘱咐我们不许到外面去说。后来,我们一家走到半路,母亲听说往北去的铁路断了,父亲就改了主意,要带我们回江西老家。
其实,父亲不去延安还有别的原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父亲也奉中共地下党指示,从江西老家省亲后,携全家老小回到南京,在“国防部”新闻局任中将设计委员。实际上,父亲还是做地下工作,直接与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联系,交换情报。
1947年到1948年,我和姐姐都在距离国民政府不远的逸仙桥小学上学。父亲虽是中将军衔,但因子女众多,全靠父亲的工薪支撑,一家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尤其是住房条件极差—在小巷子里租了两间总共不到30平方米的木板房,蜗居下全家七个孩子、两个大人。屋内木板墙缝中全是臭虫,一到夜间即肆虐横行在被褥上下。
1948年,国民党政府首次选举总统。“大选”声势浩大,高音喇叭遍布南京全城大街小巷,从早到晚播送着参加竞选的“国大代表”名单和他们的“辉煌履历”,无非是为了多拉选票。我们的学校因与国民政府仅二里之遥,因此不堪其扰,上课时只能紧闭所有门窗,可广播声浪仍是不绝。我在那小小的年纪里,已经熟知蒋中正、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等名字。没想到事隔整整60年后,2009年,我竟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电影《建国大业》中,饰演了当年竞选活动中的总监票人于右任,电影重现了当年大选总统的情景,拍摄地点也在当年南京的中央大学礼堂。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江河日下,南京日显乱象,我十岁的童年里留下不少对那个时代的深刻记忆:金圆券出笼—去菜场跟着母亲买小菜,母亲吃力地提着一大布袋纸币,只换回来一个菜篮子底儿的蔬菜,全家一天两顿都不够吃,抢米—物价疯涨,街上米店关门,邻家两个男孩仗着年轻有力气,随许多市民砸开米店,抢回两袋大米,看我们家孩子多,也不会去抢,便送了我们一袋。父亲给钱他们都不要,说那些钱是废纸,连烧火都没用。那年头,多少好人都不得已变成了“强盗”。
即便如此艰难,父亲还是日夜奔忙,终日神情严肃,言语很少,经常穿着美式中将戎装进进出出。母亲只操劳家务,很少过问父亲的公务和社会往来。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爸爸的事别问。
一到晚上,经常有一个挑着担子、边走边摇着铃子的人,在门口叫卖馄饨。父亲听见铃声就叫我或者姐姐端一个小锅,去买馄饨,馄饨成了几个小弟妹们的夜宵。直到解放后,我才听父亲说那个端馄饨的锅底是夹层的,里面装有情报,卖馄饨的人是中共地下党。
父亲也经常在夜间穿着美式中将军服外出,天亮才回来。解放后,父亲说那是和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交接情报,每次是由使馆的车在南京城僻静的郊外接送。当时姐姐和我只有十岁左右,完全不知道父亲的作为牵系着多少重大而危险的使命。
父亲是我的榜样。他一生清贫如洗,忠于信仰,廉洁正直,不卑不亢。他在晚年时谆谆教诲子女们:“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没有任何财产,只希望你们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要大学毕业。”他亲笔书写家训:名利场中甘无我,知行道上不让人。这是他给子女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迎接解放,
感受子弟兵与国民党败兵之不同
三大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告终。解放军渡江南下在即,南京以及江南大片国土行将解放已是大势所趋。
考虑到我家子女众多,怕在可能发生的战事中无辜受损,中共地下党指示父亲将我们一家大小迁回乐平老家等候解放。这是抗战胜利后,我第二次回故乡。
邻家彭老太太的独子是我的学长,大我六七岁,已是高三年级。他经常听来一些长长短短的小道消息,总是最快地传给我。
“金圆券不能用了,街上的人都用‘袁大头’和‘孙小头’换铜板用。”母亲果然再不用提着成捆的金圆券去买菜,手上的小布袋里换成了沉甸甸的大清龙花铜板。
“明天要过兵了,从浮梁专区那边来的,都是伤兵,告诉你妈赶紧买些米菜存着,要过好几天呢。”“伤兵过兵”就是从前线退下来溃逃的国民党军人路过。当时的乐平城中,几乎所有百姓都听说过国民党伤兵的诸多恶行。在老百姓眼中,他们就是祸害百姓的豺狼虎豹。
彭哥哥还告诉母亲,最近先不要让我和姐姐去上学,外面太乱。那些伤兵厉害得很,见东西就抢,还糟蹋女人。街上的店铺全关门了,乡下人都不敢进城了,小菜都买不着。县上几个有钱的大户都在往南昌和乡下搬家运东西,他们门上日夜都有扛枪的人守着,邮政局已关闭,恐怕北边的队伍快要过来了。
父亲把我们安置在乐平后,又去了南京,音信全无。母亲焦急万分,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前后门紧闭。我要和姐姐去街上看看情况,母亲没等我们说完就斩钉截铁地阻止。那些国民党军的败兵、散兵、伤兵像凶潮恶浪一样涌来,席卷了街上所有的店铺,给乐平县的百姓留下了如山的污秽后,溃逃得了无踪迹。
母亲很紧张,好像随时都会发生什么大事,她把几间屋子的油灯全点起来,通宵达旦不熄灯火,不让我们脱衣睡觉,她自己则警觉万分地坐在堂屋里,彻夜不眠地听着黑夜里的每一点儿动静。
夜半时分,大门外的石板路上,骤然响起很多人的脚步声和车辆驶过的隆隆声。母亲在昏昏欲睡的晨曦中,被一种细弱但很清晰的声音唤醒,她疑惑地移步窗前,撩起窗帘一角向西院看去,惊奇地看见四五个穿着土黄色军衣的人,背向着窗户,抱着一大捆青绿色的细竹条和稻草绑扎成的大扫帚,帮助百姓打扫院子。
军人们站成一排,从西面的院墙边儿,挥舞着大扫把,一点点扫过来,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正面,同时发现他们黄色布帽中间别着一枚红色的五角星。他们胸口的小白布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很扫兴地嘟囔:“不是八路军啊。”母亲突然变得权威起来:“没错儿,都是一回事儿。我听你爸爸说过。”街上还传来了锣鼓和鞭炮声,这象征着有喜庆的大事发生。
“嘭嘭嘭”,有人敲厨房的小门。“房东大嫂,你家的水缸在哪里?”两个身穿军衣的年轻人,扎着皮带卷着裤腿,肩上压着一担大木水桶。县上乱哄哄的,原先送水的老七已经几天没来,家里的水越来越少,全家已经两天没有洗过脸。两个挑水的军人看见半埋在地下的大水缸,不由分说就挤到缸前,麻利地把水倒进缸里,抬起满是汗珠的脸:“大嫂子,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别害怕。”母亲不知道说什么好,倒出一把铜板塞给两个军人。他们像被蝎子蛰了一样,摇着手飞快地跳出门外,后面的军人经过我面前时,摸了一下我的头,还说叫我去找他们玩儿。
街上已经有人的喧嚷和走动声,很快地,我们听到四邻说,解放军给他们都送了水,还把附近的两眼老井掏净了污泥,不用再花钱去买水了。又听说很多解放军还住在露天里,坚决不到可以住不少人的学校教室去住,说不能影响小学生们上课,夜里都睡在冰冷潮湿的操场上。
母亲的心绪明显地好了起来,同意打开紧闭了多日的大门。石板小街上,四邻的院门都相继打开。
“解放啦!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乐平,这个与中国瓷都景德镇毗邻的古老县城,被写有这些文字的红绿标语装点得春意盎然,乐平人也被这些口号鼓动得心潮澎湃,如获新生。■
(责任编辑 王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