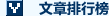热血学生走向前线的故事
明朗
结伴去延安
我的家乡在山清水秀的汉中,北有秦岭之险,南有巴蜀之富,是刘邦赖以建立强大汉王朝的根据地,是诸葛亮北拒曹魏的前敌指挥所。我的父亲明益伯,是清末洋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当了20年的数学教员。我自小就随父亲在南郑念书,考入初中那年,父亲去世,我们兄弟二人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日子。
读中学时,我是个埋头读书的学生,但又和当时多数中学生一样,有点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感到了民族危亡,为此奔走呼号;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感到不满,对共产党红军,有模糊的钦佩之感,想知道其更多的东西。
1935年夏,我高中毕业,在县中谋得文书一职,月薪二十元大洋。一年后,我带着积攒的百余元钱,和弟弟明吉顺、同学李之实到西安投考大学,不幸名落孙山。后教育厅招考电化教育人员,我名列第一,录取后,被保送到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学了两个月电影放映。毕业后回到西安等待分配。这时,我和弟弟明吉顺、同学李之实住在一家名为西北公寓的小房间里,做着分配后每月可以拿60到100元薪金的美梦,甚至连找哪个姑娘结婚都谋算到了。
一日清晨,天还未亮,在我们住的公寓附近,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一时间,似乎整个西安都被枪声笼罩了。我们几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不敢外出。天蒙蒙亮的时候,枪声渐渐稀疏,只听得街道上还有人在奔跑,喊叫。到了八九点钟,枪声停了,外边也有了说话的声音,我们才走出房间。门口已聚集了一些人,都在猜测议论,谁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十点过后,有人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张“号外”跑来,大家围拢过去抢着看。“号外”登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消息和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我们当时还不懂“兵谏”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把蒋介石捉住了。隐约觉得,这一下好了,要抗日了。人们兴奋地跳起来,多年压抑着的抗日热情,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沉睡的古城顿时沸腾起来。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事变后的几天,我们跟着西安的学生奔走活动,到革命公园参加大会,听张学良、杨虎城赤胆为国、大义凛然的讲话;宣传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喊抗日的口号,唱救亡的歌曲;看一批批开赴潼关前线的东北军、西北军队伍的誓师行列;走街串校打听事态发展的最新消息。
但是,当我们夜晚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发现“经济恐慌”正向我们袭来。口袋里剩余的钱不多了,公寓老板催要房租,饭也不给开了,每天只能买半个锅盔、一块豆腐乳,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百无门路,明知无望,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教育厅想办法。但事变后的教育厅不认以前教育厅的账,交涉的结果是,不但眼前救急的希望破灭,连将来有没有电化教育这回事也渺茫了。
人总是要吃饭的,三个人,三张口,没有钱,不管西安如何沸腾,这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于是,我和李之实背着弟弟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这时,红军已到了西安城外,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简章也传到了西安城内。我们弄到了一张油印的广告,虽然纸很粗糙,印刷也略差,可是这张广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们对这张广告一个字一个字地揣摩推敲,考虑着是否要走这条路。
当时,我们明白这是一条冒险的道路,吉凶难定,前途未卜。然而,由于当时整个西安抗日浪潮的推动,也由于李之实(曾经参加过红军外围组织—“红友社”)的劝说,加之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我终于一拍桌子,下定了决心。
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弟弟也带去冒险,且家中还有孤零零的老母亲,按理也应留一人在家尽孝。于是,我把仅有的几元钱交给了弟弟,说服他和其他几个同乡同学结伴回了汉中。
等弟弟一走,我和李之实二人饱餐了一顿羊肉泡馍,就离开西安,渡过渭河,赶到了三原。红军负责招生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元钱,让我们自己到延安去报到。在填写报考表格时,我们两个人都把名字改了。李之实改名李红,表示他已经参加红军了。我一时不知改什么好,抬头见墙上糊着一些旧报纸,内中有个大标题叫“华北明朗化”,于是灵机一动,把名字改成了“明朗”。
在一个冷风刺骨、飞雪扑面的早晨,我们一行十几个穷学生,结伴踏上了白雪皑皑、一片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
第一次见到了
红军部队
到达鄜县(后改为富县),我们才第一次见到红军的部队,红军也才第一次招待了我们。这里的红军指战员虽然衣着不统一,补丁也不少,却很整洁。有的脚上穿着布鞋,有的穿着草鞋。有些草鞋前边的“鼻梁”上,还用红布条扎成一朵缨子,走起路来一闪一闪的,颇有英气。出面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跛着腿的干部,可能是打仗负过伤,人很和气、很热情。我们一路上都是在老乡家里过夜,现在到了红军部队,战士们忙着给我们打水洗脸、洗脚,抱草铺炕,招待我们喝水、吃饭,晚上围在屋里问长问短,打听白区的情况。虽然有些拘谨,但我们心里却觉得暖烘烘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给我们盛菜的盆子,竟是我们洗脸用过的盆子,是个很旧的洋瓷脸盆,周围的瓷釉大都脱落了,只留下盆底还有不大一块花纹,所以不难辨认。从鄜县到延安的路上,我们多次受到红军接待,渐渐发现,原来用洗脸盆盛菜、盛饭,是普遍的现象。有几次我们发现,甚至连洗脚也是用同一个盆子,渐渐地,我们也不再大惊小怪了。
到了延安,条件就更艰苦了。那时的延安,房倒屋塌,瓦砾遍地,人烟稀少,草木凋零。街上有两三个支着临时锅灶卖羊肉水饺的摊点,算是唯一兴隆的商业了。我们住在东门外一所旧营房里,两排通炕,无门无窗,也没有被褥,一到晚上,寒风吹得呼呼叫,全靠炕上铺的麦草取暖,人挤人,人靠人。遇到下雪,雪花也能飘进屋子,飘到身上、脸上。吃的是有霉味的陈小米,上顿红萝卜丝,下顿红萝卜片。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面前,有些人动摇了、后悔了。
抗大二期有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的学员是红军干部,住在城内;四大队由白区来的青年组成,大部分是学生,小部分是东北军、西北军的青年军官或学兵队的学员。四大队的大队长是聂鹤亭,政委是董必武,下辖九、十、十一共三个中队(即三个连),我被编在第十中队,中队长是边章武同志。
大约在三四月间,董必武同志给我们讲话,谈到有些人想回白区的问题。他把眼前的困难讲得很实际、很具体,把共产党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道理讲得很深刻、很坚定。他的话朴素、诚恳,让人听了以后,不能不为共产党红军这一批人历尽艰辛、舍生忘死、矢志不渝的救国救民精神所感动。讲到最后,他说:“想回白区的可以回去。我们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有的人回到白区,和我们这里比一比,如果觉得还是这里好,再回来,我们同样欢迎。”听到这样仁至义尽的讲话,很多人湿了眼眶。
可还是有二三十人离开了延安。其中有一位,是我的汉中同学。面对延安当时那样艰苦的生活,红军那样窘促的局面,我思想上也有点动摇,同班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学察觉后,对我说:“一个人,要革命,就不能反革命,要反革命就不能再革命,最可怕的是又要革命又要反革命。”这几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坚定了我留下的信心。
美好的延安生活
进入四月的延安,春意渐浓,柳拂嫩丝,草萌新绿。由于通了汽车运输,我们刚来时吃的发霉的小米,已被一部分白面和大米代替,每个礼拜有了一顿“会餐”。所谓“会餐”,就是在平时的土豆、红白萝卜之外,加两盆猪肉或羊肉做的荤菜。延安城里还开了个合作社,有零钱的人,半月或一月可以去吃一碗扣肉,肥肥的几块,颇为解馋。加上天气转暖,寒冷的威胁已基本过去。总之,比我们在西安顿顿吃锅盔加豆腐乳的生活要好多了。
在抗大,最使我们满意的,是学习和民主平等的生活。学习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这些课程的内容对我来说,绝大部分是生疏的,一个崭新的知识领域在我的眼前展开了。讲课的人都是很难得的教师,毛主席讲哲学,朱总司令讲游击战术,吴亮平讲列宁主义,董必武讲中国革命史。董老是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讲课时,联系自己的经历,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讲到红军长征,有血有肉,引人入胜;朱总司令用他的实战经验讲游击战术,深入浅出,使我们这些完全不懂打仗是怎么回事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毛主席讲课是全大队在一起听,还有许多从城里来听讲的人(包括陈赓、罗瑞卿等),大家围坐在一个坝子里听课。那时,没有扬声器,主席的声音也不算大,可是,除了听到有趣的地方,发出的阵阵笑声外,从头到尾大家都认真听讲,无一人讲话,主席讲的每个字、每句话,都能清清亮亮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毛主席讲哲学,旁征博引,善于用一些具体事例,阐明深奥的哲学道理。他不仅引用近代革命的事例,而且还引用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例,如《水浒》《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等。听课的人有一些是会速记的,把毛主席的每次讲课内容速记下来,加以整理,找人刻在蜡纸上,油印成册,以后经过修改,便是收入“毛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不过,讲课时许多风趣的实例,已经删去了一些)。我在中学里刻过蜡版,就毛遂自荐,参加刻了一部分。多年之后,我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看见陈列品中有当时的一份油印底稿,其中有一张竟是我刻的。
还有周恩来同志,那时在国民党区域办“外交”,每逢从“白区”回来,就要给大家作报告,讲外边的形势。印象最深的是讲西安事变,从事变的发起到和平解决,再到今后的展望,一连讲了四五个小时。听的人个个全神贯注。周恩来作报告时,没有稿子,可是讲出来的话,就是一篇用词考究、推理严密、思想深刻的好文章。听他的报告,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是极高的精神享受。
抗大的课外生活也很丰富。学员们自编墙报,举行篮球比赛,一有时间,还组织汇演,演出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演出时,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也会和大家一样,坐在台下的矮凳子上观看。进入六月,还能到延河里洗澡、游水。
在抗大,我收获颇丰。首先,我被共产主义的真理完全征服了。这是一个知识宝库,是继承了人类思想的精华而总结出来的无比正确的理论体系。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从理论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绝非权宜之计。其次,我被共产党、红军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生活深深吸引。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传奇式人物竟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个个都很有学问、有本领。听他们的讲课和报告,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说:“共产党里面真有人才!”这时,我们已见到成仿吾、丁玲等文化名人,听过他们讲话。我心里想,这样的人都到红军这里来做事,可见我走的这条路是绝不会错的。
在抗大近半年时间的学习,使我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从为找出路来到延安,变成自觉地、坚决地要走革命道路了。这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延安的实际生活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也是对每一个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起到的作用。
我们要抗日救亡!
卢沟桥的枪炮声,传到了延安。四大队的学员群情激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把人的喉咙都喊哑了。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抗日救亡的责任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学员们的心已经飞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再也无法安心学习。当时的领导人,似乎和学员们想到一块去了,大队长聂鹤亭同志宣布提前结业,分配工作。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的热烈拥护。
我被分配到“援西军”。我们一百多人编成一个队,由王维舟同志带领,奔赴前方。那时的前方部队在渭河以北集结。我们走的还是去延安的老路,一路上见到好几批青年向延安进发,一个个都是生龙活虎的样子。我故意用话吓他们:“延安的生活可是艰苦啊!”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道:“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艰苦!”
这是民族的正气!我受这股正气的感染,到达前方部队,打听到汉中的邮路已通,于是提笔给弟弟和家乡的同学写了一封信,鼓励他们到延安来,到前线来,杀敌报国。
事后知道这封信引起了很大反响,弟弟明吉顺和家乡的许多同学,跟随全国知识分子涌向延安,也踏上了奔向陕北的道路。
换帽子,开赴前线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要求部队改编换帽子。宣传队的几个红小鬼,为此伤心得哭了。一个外号叫“小老头”的伏在我的腿上哭,一直不肯把头抬起来。他的家里很穷,爸爸和哥哥都被敌人杀害了,妈妈上了吊。他是作为孤儿,跟随红军,被红军收留的。现在,看见帽子上的“红五星”换成了“青天白日”,他怎么也想不通。我们只得用民族存亡的大义来开导这些小鬼,别的话他们都难以接受,只有刘师长在检阅时,讲的一句话,“我们是西瓜政策,外青内红”,他们能听得进。这个比喻又浅显,又形象,又妥切,似乎打开了这些小鬼的心扉,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种下红军的本质不会改变的信念。
老同志们包括那些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含着泪珠,把自己的红帽花、红领章拆下来,洗得干干净净,抚得平平板板,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包了又包,妥妥贴贴地放在自己背包里。我们为这种朴实真诚、忠贞不渝的阶级感情所感动,把自己的领章、帽花也洗干净,妥贴地保存起来。
部队改编后,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当教员。到了随营学校,分配到一营的一连当文化教员。这个连的学员,大部分是西路军失败后,逃回来的干部。秦基伟同志编在这个连里当排长。上课的时候,逢到他值日,他就喊“起立”的口令,立正向我敬礼。听别人说,他是西路军一个主力团的团长,是很能打仗的,这样的人向我敬礼,我有点诚惶诚恐,无奈这是军队的规矩,只得也按规矩还礼,眼睛却不敢正视。以后,次数一多,也就习惯了。这些工农干部在一起,似乎一切都随便得很,简单得很,全然没有大、小、尊、卑的区别。他们还有个奇怪的“嗜好”: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抱在一起摔跤;即使乍见面的熟人,也二话不说就抱在一起较量;谁把谁摔倒在地,就压在那个人的肚子上,要他认输,这样来表示亲热。这种不分等级、不择场合地同志间的戏耍、打闹一定程序上密切了战友关系。秦基伟同志在我们到达阳泉后,就调去领导正太路的游击支队了,后做了太行二分区的司令员。我一直没见过他。1945年日本投降,他在太行一分区任司令员,我又随他带的部队攻取了赞皇、元氏、临城等县城。
过黄河时,战斗部队先行,随营学校属师直,是二梯队,过河后,在侯马一带集结。这里的老百姓比较富裕,据说在外经商的居多。窑洞式的住房颇为阔气,窗子上、炕沿上、墙上、箱柜上饰有各种颜色的花纹图案,屋里屋外干净清爽,人的衣着打扮也比陕北整齐、时兴。
这时,敌人已快打到娘子关、雁门关了,侯马是同蒲铁路的一个站,过路列车很多,都是装运伤兵和携带箱笼衣物向南逃难的人。
忽然,传来平型关歼敌的捷报,我们立即向群众宣传,这是八路军打的,八路军就是以前的红军。八路军打了大胜仗!顿时,人人喜形于色,欢欣若狂,争抢着要我们的捷报传单。他们亲眼看见一批一批都是向南溃逃的国民党官兵,唯独我们这支戴着“八路”臂章的军队,偏偏不怕死,要往北开,对我们就分外热情。有几天,我们的伙食单位,简直用不着开伙了,因为,三三两两的都被驻地的老乡拉到家里去吃饺子、吃面去了。我也遇到几次,一家老老小小都来请,连推带拉,实在无法谢绝。到了老乡家里,一定要吃个菜足饭饱,才准离开。不仅是我,所有被请的人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抗日军人的莫大光荣。
在侯马,我们还得到了一些物资补充。阎锡山大概眼看仓库里的东西保不住了,慷慨地发给我们每人两套军装、一顶斗笠、一副绑带、一个挂包及一条子弹袋。这些装备全是黄色的,部队集合,顿时变成黄灿灿的一片。这样整齐划一的崭新服色,对红军来说恐怕是破天荒了。可惜,武器方面,只补充了子弹、手榴弹和一些步枪。
我们穿着一色新的服装,上了往北开的火车,乘的是一列装煤、运货的敞车。车厢挤得满满的,白天,人像木头一样,一个个竖着,到了夜晚,横七竖八地躺在里面,人压人、人叠人。你的头枕在我的腿上,我的腿压在他的肩上,一点儿空隙都没有,更不要说翻身的余地了。车厢里的气味,更是难闻到了极点。
好在,这时的火车已打破靠站停车的常规,只要不是让车,就一直往前运行。夜晚转入正太,第二天上午到达阳泉。这里已能听到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车站内外满是伤兵,不是头上缠着绷带,就是腿上捆了夹板,一个个蓬头垢面,有架着棍子跛腿行走的,有躺在地下呻吟的,有来回走动的,有蹲在角落吃东西的,喧嚷声、扯着嗓子骂娘声,乱成一团。这些伤兵,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麇集在车站附近,等候向后转运的列车。我们一下车,伤兵们就争先恐后地往列车上爬,你推我搡,哭叫呼喊,惨不忍睹。
这时,突然发现敌人的飞机,到处响起了滴滴滴、嗒嗒嗒的防空号音。我们已离开车站,跑步朝南面的山地一带疏散。
其实,这次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阳泉车站,我们已到了南面的山地,所以,没遭受任何损失。干部、学员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对于此是不大在乎的。
经平定向昔阳的途中,同志们仍在议论空袭的事。有的说,阳泉车站的伤兵可惨了;有的说,他端起机枪打了一梭子,不知打着没有;有的开玩笑称,是他拿步枪把飞机打跑的。
接着,传来我军夜袭阳明堡,焚毁敌机二十余架的捷报。这一仗是我们师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打的,自然使人分外兴奋。同时,也传来指挥夜袭的三营营长赵宗德同志为国捐躯的噩耗。学员中有些人认识赵宗德同志,大家为他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们默默致哀。
收容散兵,扩大队伍
七七事变以来,除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和阳明堡打了两个胜仗以外,几乎没听说中国军队在哪里打过胜仗。号称天险的娘子关失守了;继忻口之后是太原陷落;平汉路方面,敌军也势如破竹,直下邢台、邯郸;同蒲、平汉、津浦三路敌人,凶焰万丈向黄河逼近。很显然,我们已处在敌人的侧后了。
党中央给八路军的任务是作战略展开,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抗战。随营学校的学员,有一部分已调出去工作了。我随一个连(大约只剩五六十人)沿太行山东侧一带活动,任务是收容散兵,扩大部队。
到了辽县(后改为左权县),群众报告,有一股土匪在下庄杀猪宰羊、抢东西、侮辱妇女,请求我军前去剿灭。我们便向那个方向开进,离下庄不远,才知是国民党军队溃逃的散兵。连的干部决定当晚进行包围,把一个连分成两摊,一部分绕到村南占领阵地,其余部队占据村北的山头。大约两三点钟光景,部队由几位熟悉道路的老乡带路,摸到了预定地点,四面山影绰绰,万籁俱寂,只有少许灯光若隐若现,标示出村庄的位置,近得简直像在我们的脚下。这时,指导员叫我喊话,顿时,沉沉黑夜仿佛突然苏醒过来,方圆几十里都发出了回响。我的话很简短,无非是说,我们是八路军,已将他们包围了,愿意打日本的,欢迎加入;不愿意的,交出武器,遣送回家;叫他们立即派代表来谈判,如不回答,就打进村去,缴他们的械。
村子里开始响起犬吠声,接着便传出派代表谈判的应诺。我方的政治教员李达(抗大二期九队的学员)和对方的代表在村口进行了谈判。原来 ,村子里不是什么散兵,而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正规营。谈判倒也顺利,他们愿意归八路军收编。于是,我们的部队开进了村庄。
进村后最突出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坏得惊人。他们住过的人家,像遭强盗抢劫过一样,箱箱柜柜全被彻底翻腾过,遍地都是丢弃的衣被杂物,家具器皿,撒抛的核桃、板栗、柿饼等干果和一摊一摊的粮食。我们担心,能不能把这伙人都带回去交给战斗部队,也担心能否把这批人改造成人民的军队。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第二天,我们带着这一营人向辽县进发,中午休息后,我们已走出村子颇远,这个营却不走了。他们显然是在长官的指挥下,拉开部队,占据了村外的山头,架起轻重机枪,准备朝我们开火了。连长、指导员只得命令部队就地停止,向他们喊话,问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走。他们回答,要各走各的路。这时,政治教员李达,还在他们那里,原意是让李达同志和那些营长们一块行动,可以边走路边做工作。连长、指导员便派我和两位学员返回去找李达,一同向他们做工作,看能不能挽救。不料,我们三人刚往回走了几步,对方就发出威胁:不准过来,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排在山坡上的十几挺机枪,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对着我们瞄准,准备射击。我们只得停止前进。连长、指导员估量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整整一个营,约五百人左右,单是重机枪就有三挺,轻机枪每排一挺;我们只有五六十人,一挺轻机枪,而且,对方已经展开,占领了制高点,我们还是行军队形,一条线摆在大路上,要是打,肯定会吃亏。于是,当机立断,让他们走,只是要将政治教员放回。但是,对方向下庄方向运动时,政治教员李达同志竟没有回来。我们认为是被这些家伙胁持走了。
我们撤到另一个村庄作应战准备。指导员赶回校部报告。校长张贤约、政委袁鸿化同志很赞赏连干部临事应变的决定,特别指出连队学员是党的宝贵财产,不能拿去硬拼,国民党的溃兵不愿接受改编就算了,只要他们不践踏群众,在哪里抗日都一样;让我们撇开这个营,沿太行东麓向南,继续 完成收容散兵、扩招新战士的任务。
我们一直到了磁县附近,沿途收容散兵,三三两两,十个八个,有携带武器的,有徒手的。根据老百姓报告,还找到一部分被丢弃的枪支弹药。收获最大是在磁县附近,那里有一些厂矿,当地党组织正在组织游击队,我们到后,便帮助他们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所以,往回走时,五六十人的队伍,扩大到将近两千人,增加了三十多倍。原来的学员变成了排、连、营的干部,成为拥有三个营、九个连的整团了。我也从连部到了团部,包办一切文字方面的工作,诸如登记枪支弹药,统计人员,分发传单、印刷品,收集书报杂志,起草通知和来往信函等,忙得不可开交,其他的干部也忙得团团转。
一天,我们在磁武(武安)交界的村子里宿营,这里离敌人较远,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连部分配我晚上带班查哨,意思是让我经受点锻炼。到了后半夜,村外的大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赶到村口哨兵站,趁着月色观察,看到有一伙人挥舞着大刀向这边走来。大刀在月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是敌是友,弄不清楚。我大喊一声:“是什么人?”对面的人不但不搭腔,反而挥舞着锃亮的大刀,气势汹汹地扑向前来。我急了,鼓起劲又大喊一声:“是什么人?”对面的人已经越走越近,连军服军帽都看得清楚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三排长赶到了,他把驳壳枪一举,拉动枪栓,命令对方:“立即停止!不停住就要开枪了!”就这一声,那几个人都乖乖地站住了。三排长厉声喝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面答道:“是孙司令的人。”三排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什么事,派一个人过来,别的人不准动!”过了一会,对方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三排长高声粗嗓地回答道:“是中国的队伍。”又等了片刻,对方果然有一个人朝我们走来,喊道:“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空手。”说着把两手举得高高的,像是要来投降的样子。
原来,前面村子里,驻扎着从平汉路溃逃到这里的孙殿英部队。他们来了六个人,是到这个村子里捉逃兵的。三排长这时才告诉他,我们是打平型关、阳明堡的八路军。那人一听是八路军,接连说了几个“久仰”“久仰”。这时,我们的部队已闻声起床,持枪赶到村口。三排长一面派人向连部报告,一面将部队部署在街道两旁,然后,叫孙司令的人进村。那几个人见这阵势,再也没敢挥舞大刀,悄悄地从村子里穿了过去,到茫茫的野地里去捉他们的逃兵了。
(本文由明朗遗孀李凡提供)■
(责任编辑 王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