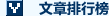20世纪60—70年代的军事战略方针调整
黄迎旭
军事战略是国家的总军事政策,具有长期稳定性;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家总军事政策在特定时期的具体化,因时而异。在1993年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出台以前,军事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针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不是很规范,常常混用,如1956年确立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就具有军事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双重含义,因而又称为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1988年提出的新时期军事战略,其性质是军事战略方针。我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这是由我国基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外交政策,以及防御作战制胜机理等根本性因素所决定的,无论时代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要这些因素没变,积极防御四个字就不会变。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则是随着世界战、和的大趋势以及国家安全环境、战争威胁、作战样式等重要因素的演变而适时进行调整,充实新的内容,使国家的军事建设和战争准备跟上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正式确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以来,曾数次调整军事战略方针,20世纪60—70年代因应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进行的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在将近20年时间里,不仅主导了国家军事建设,而且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全局,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
此次调整军事战略方针,是逐步进行、分步实施的,从提出备战整军,到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把整个国家发展纳入到备战轨道。1980年10月,邓小平在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这标志着20世纪60—70年代所确立和执行的军事战略方针将被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所取代。
“备战整军”
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国家安全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毛泽东虽然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应付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各种准备,但基本判断是“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中国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依据这一基本判断,国家工作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军事建设置于服从地位。毛泽东在1956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大幅度压缩国防费,把更多的钱用于建工厂、造机器。那个时期的军队建设全面贯彻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所提出的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努力建设一支能够应付现代战争的革命军队。1956年制定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要旨是“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国家军事政策、国防部署、军队建设、作战思想等都要适应争取和维护长久和平的要求。
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改变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看法趋于严峻。导致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两党分歧逐步演化为国家对立,苏联终止全部对华援助,特别是终止执行旨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技术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偏袒印度,背离同盟约定。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在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边民越境出走,威胁我国边境安全。中苏关系恶化,使我国因中苏同盟关系而享有的“背靠沙发”的安全态势不复存在。有鉴于此,我国开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把准备打仗提到了议程。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建议会议“接触一下”军事问题,并提出“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争取“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一个吓人的东西”。1月22日至2月27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传达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分析:大的战争,原子战争,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目前的可能主要是打不起来;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威胁就依然存在。依据这个判断,会议讨论了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形成了1960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林彪在会议上针对美蒋可能发动的进攻,提出把“北顶南放”作为指导国防建设的战略方针,要求根据敌情我情加强国防建设,突出重点。这是一次动员和部署“准备打仗”的会议。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发展遭遇重大挫折,国家安全形势也趋于紧张。首先是台湾蒋介石集团以为有了可乘之机,蠢蠢欲动。1960年9月国民党在台湾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提出“反共复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要求“加速完成各种准备,迎接胜利”。会后,台湾当局开始大造“反攻复国”舆论,并加紧进行“反攻”军事准备。1962年初,蒋介石成立以他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最高决策机构。国民党军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连续进行有美军参加的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把岛内战争气氛推向高点。在此期间,印度也企图借中国内政外交出现的困难局面实现自己的领土野心,从1962年初开始大力推进所谓“前进政策”,试图通过加大军事压力,迫使我国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退出阿克塞钦地区,中印边界全线紧张,流血事件频发,把自1959年开始的中印边界地区的军事对峙推到战争边缘。此时,美国没有袖手旁观,它虽然萌生了利用中苏失和拓展自己战略利益的企图,但又认为中国的“好战”性格对其在东南亚的控制权构成威胁,因而于1961年升级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行动,开始实施“特种作战”,并插手中印争端,公然承认麦克马洪线,给印度提供武器装备,同时对蒋介石的“反攻行动”采取暧昧态度,而一些美军将领则公开表态支持蒋介石,渲染台海紧张气氛。
1962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提出“整军备战”方针,要求按照这个方针调整军队编制,将作战师分为值班师、普通师、教导师,以提高军队的战备水平。值班师满员齐装全训,配备在第一线;普通师编两个大团,配备在第二线,半训练半生产;教导师编3个小团,配备在第三线,主要搞生产,训练民兵。随后,中央军委召开编制装备会议。会议从2月开到5月,先在广州开,后搬到北京开,围绕着“整军备战”研究讨论军队整编、装备以及军工生产等问题。会议涉及到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有责任的国防工业、战备动员等问题,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毛泽东得知后指示,把“整军备战”改过来叫“备战整军”[1]。用备战来统一认识,会议加快了进程。会议就军队编制,制定了南轻北重、前轻后重、下轻上重、机关轻连队重(前三条关于装备,后一条关于人员)的指导原则,以使我军能够既适合于进攻又适合于防御,既适合于山地又适合于平原,既适合于白天又适合于夜间,既适合于战斗又适合于运动,提升部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会议期间,中央军委鉴于东西两个方向紧张局势加剧,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之策,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中印边界方向采取稳定方针,东南沿海方向作为重点,采取紧急战备行动,防备蒋介石铤而走险。5月3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东南沿海地区战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实行紧急战备的八项措施,要求部队从物资和思想上做好出动准备。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强调不管敌人来不来,都要认真充分地做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侥幸心理。
确立“备战整军”方针,拉开了我国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战备行动的序幕。1960年初,全军员额270万,编制装备会议后军队进行整编,经过2年多时间,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压缩了院校,理顺了指挥领导体制,同时军队规模得以扩张,到1965年初,全军员额达到447万,增加约65%。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紧急战备指示,军队立即开展战备动员,进行应急战备训练,调运战备物资,加强战场建设,全军迅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但贯彻“备战整军”方针和进行紧急战备,并没有改变国家工作整体布局,经济建设还是摆在重心位置。周恩来于1962年6月在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说:就战争威胁而言,东南亚是一个方向,是我们和美国长期进行争夺的地方。美国在这个方向有三种可能的战略方针,第一种是核武器战略,威胁全世界;第二种是局部战争,哪个地方便于发动,就在哪里发动;第三种是特种战争,美国人出面,用反动的游击战争消灭革命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个是朝鲜,美国重新挑起三八线战争。目前叫嚷最凶的台湾当局,要反攻大陆,美国用两手,一方面反对它反攻大陆,一方面又扶持它。估计有四种可能,第一种是蒋介石先出头,作试探性登陆,然后逐步扩大;第二种是如果试探失败了,美国有可能搞掉蒋介石,甚至自己直接出兵。在这两种可能中,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大,然后才转入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是,美蒋一道来挑起全面战争,而这种可能性不是首先的,要看前两种可能的发展。还有第四种可能,就是我们准备得好,也有可能推迟。周恩来还说:“现在看,美帝国主义也没有准备好打局部战争。一打就分散了它的力量,目前还没有看出它决心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2]周恩来的这番话代表了中共中央对战争威胁的基本判断,基于该判断的“备战整军”方针,说到底,是一个控制危机升级、应对局部战争的方针,重点是防范东南沿海方向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反攻大陆,兼顾西南中印边界方向,同时又作最坏打算,准备由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在此期间,我军成功地粉碎了蒋介石集团的小股武装窜犯和海空袭扰,同时在西南方向打赢了中印边界自卫还击作战,而这些作战行动均属于局部战争或局部作战行动。
“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到1960年代中期,虽然蒋介石反攻大陆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印边界紧张局势也得以缓解,但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在总体上却更趋紧张、更趋复杂。美国在“特种战争”严重受挫后,于1964年初开始酝酿扩大侵越战争,4月间形成了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的战争计划,并先行升级了在老挝的侵略行动,印度支那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5日,美国借口所谓美舰受到攻击的“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把“北炸南打”战略付诸实施。苏联则在中国北面舞枪弄棒,中苏边境地区的火药味渐浓。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随即进驻蒙古。1964年上半年,中苏边界谈判中止后,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地区调集兵力,同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边界摩擦事件逐渐增多,中苏对立有了军事对峙的味道。
首先引起我国高度警觉的,是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我国一直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保持警惕,认为这些活动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并认为美国有可能从这个方向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我国对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行径的反应,就是坚定地支持越南抗美。早在美国紧锣密鼓筹划升级侵越行动时,中共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越南的反侵略行动。6月间,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说:“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3]以后又对相继来访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范文同表明了同样态度。从此,中国对越南实行了长达12年的大规模无偿军事援助,先后派出防空、后勤、铁路、工程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人次,提供的物资总值(按照当时国际价格计算)达200亿美元。在大力支持越南抗美的同时,我国提升了战争戒备程度,以防美国恼羞成怒,把战火烧到我国。毛泽东是从抓战略后方建设推动新一轮战争准备的。早在5月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管理处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三陵会议),他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抓军事,一个是培养接班人。关于地方抓军事,毛泽东强调各大区、各省要抓民兵、修械厂、军工厂等,不能全靠中央。8月6日,美国开始实施“北炸”翌日,毛泽东在审阅谴责美国战争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时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毛泽东放弃了骑马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的计划,准备应付可能的战争局面。在加强提防美国的同时,我国把防备苏联也提到了议程。1964年4月总参谋长罗瑞卿鉴于中苏边境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新疆地区的战备方案,提出苏联在我北部边疆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可能有二,一是防御性的,二是进攻性的,而前者的可能性大,但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打,有大、中、小三种可能,中、小打的可能性大,但我们要准备它大打,以确保主动。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4]。在此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不仅要防备东边的帝国主义,也要防备北边的修正主义,防备它们合伙整我们。
依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以及备战升级,我国再次调整军事战略方针。
一是由准备应付局部战争转变为准备应付正在迫近的有核背景的全面战争。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交战,必须举国迎敌,这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全面战争;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握有核武器,同它们交战必然是有核背景的战争,要准备它们使用核武器;美、苏咄咄逼人,要准备它们早动手。毛泽东在十三陵会议上讲“准备打仗”问题,所要求的就是做举国迎敌准备。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提出“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准备两面都打”。5月间,中央军委召开全军作战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打与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备上面;美国和苏联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要准备苏联参战;打不打原子弹,要放在打原子弹的准备上面;迟打还是早打,要准备早打。以后,这个方针逐渐被表述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应该说,当时对战争紧迫性的判断还是留有余地的。周恩来在接见出席全军作战会议人员时说:“今天的战备会议,大家都想到战争会来得很快,会大打,会当年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甚至打核战争,这些都是从最坏处打算,我们要做这个准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打得快,打得大,打核战争,两面都打,是不是马上就来呢?不是,还有一个过程”[5]。但在战略指导上则必须立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情况,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要从困难着想”,“不妨把困难想多一些,想尽”,惟有如此,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二是由“北顶南放”转变为“诱敌深入”。林彪设想的“北顶南放”,以长江为界,对从朝鲜半岛和黄海、东海北部方向来犯之敌,坚决顶住,寸土不让;对从中南半岛、南海和东海南部方向来犯之敌,则放进来打,切断退路,围而歼之。毛泽东在1964年以后思考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方针,否定了“北顶南放”,认为“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走日军老路?我看不一定。从广东来,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6],而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中间突破”,一是从天津上来,奔向北京;一是从青岛上来,奔向济南;一是从连云港上来,奔向徐州、开封、郑州;一是从长江上来,奔向南京[7];从而把我们南北切断,地区分割。应付敌人的“中间突破”,毛泽东主张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是要顶一下,顶不住就走,但重心不能放在顶的上面,而要放在把敌人放进来打的上面,先是消耗敌人,待扭转敌我力量对比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套打法就是“诱敌深入”。这套打法的好处是,可以发挥人民战争优势,扬长避短,是我国实行积极防御的有效办法。实行这套打法,就要求搞好地方武装力量建设,各大区、各省都要建设自己的“小三线”,准备一旦被分割能够各自为战,独立应敌。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又预计到诱敌深入可能不灵,因此要两手准备,既要准备在沿海地区打,又要准备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国土纵深地区打,但战争准备要立足于诱敌深入。
三是把战争准备重心放在战略后方建设上面。1964年4月,总参谋部作战部经过调研提交了关于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防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问题很突出:(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集中在14个百万以上人口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而且这些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建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8]。这个报告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迅即研究所须采取的措施。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搞三线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要快,并说“攀枝花搞不好睡不着觉”。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准备应付敌人的大规模入侵,一个是战略方向问题,一个是战略后方问题,各省要有自己的战略后方(小三线),国家要有国家战略后方(大三线),并称之为“靠山傍水扎大营”,搞好了,反侵略战争就有了可靠支撑。毛泽东曾提出:“要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厂,三不准备打游击战,只是仓促撤退。要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他没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国生活的,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才保住重庆。”[9]苏联在战前不重视后方建设,打起来才匆忙把大批工厂从西部搬到东部,造成战争初期的混乱和被动;蒋介石在抗战中从东南退到西南,只搬去很少一点工厂,大部分没有动,因为他完全指望外国援助。从这段话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关于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的基本考虑:第一,建设好战略后方,可以避免战争初期的被动,并为持久抗敌提供物质技术支持;第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赢反侵略战争,把民族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必须建设强大的战略后方。
这一次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牵引军队建设全面转入临战准备轨道,部队训练、武器装备发展、战场建设、后方基地建设、物资储备等都向“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聚焦,军队编制随之进一步扩充,规模日益庞大。与此同时,我国加快了研制尖端武器的步伐。1962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提出的1964年、最迟1965年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报告。1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负责原子弹研制的专门委员会(专委),调集全国力量保证实现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的目标。专委先后9次开会,研究解决有关问题。在专委领导下,动员了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1000多个单位的技术力量,安排制造原子弹及导弹所需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2万余项,大大加快了研制步伐。1964年4月,成立了以张爱萍为总指挥的核武器试验指挥部。9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专委会议安排核爆试验,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早试和择机再试两个方案中选择前案。9月2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10月进行核爆试验。随后,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专门研究核爆试验时间,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响。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炸响。随即,我国开始了原子弹小型化研究,并加快中近程导弹研制。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1974年8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列装。这一系列重要成就,使我国拥有了真实可信的战略反击力量。
这一次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引发的更大效应,是国家经济建设被纳入战备轨道。1965年恰值我国正在制定“三五”计划(本应1963年开始执行“三五”计划,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还需调整,因而推迟到1966年开始执行“三五”计划)。最初设想的“三五”计划是优先考虑发展农业,兼顾国防,然后从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出发安排重工业,因而被称为“吃穿用计划”。毛泽东提出建设“大三线”任务后,国家计委开始改变“三五”计划编制思路。196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关于“三五”计划设想汇报时指示:“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10]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三五”计划的新设想,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应是一个以战备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这个设想得到国务院认可。随后,正式形成了“三五”计划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项目大部分安排在作为战略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11]。这个计划安排得到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同意。毛泽东于1966年3月12日给刘少奇去信,提出农业机械化“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而这实际上是对“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的高度概括。“三五”计划后来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但这个计划的核心要旨“把国防建设摆到第一位”,还是得到了贯彻落实,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在一个时期内放在了战争准备上面。
“要准备打仗”
1969年3月2日,侵入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的苏联边防部队率先开枪,中国边防部队实施反击,打死打伤苏联边防部队60余人,自己牺牲17人,伤35人,失踪1人。15日、17日双方再次激战,苏军先后付出伤亡170余人的代价,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2人,负伤27人。珍宝岛事件是中苏边境地区局势持续恶化的结果,虽然武装冲突规模有限,时间有限,但影响巨大而且深远。
苏联迅速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在不到1年时间里,其驻扎在亚洲的陆军师数量增加到70多个、100余万人、2万余辆坦克,空军各类飞机数量增至3000余架,海军各类舰船增至800余艘。9月初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中亚军区,并调换了中苏边境地区各军区和军兵种的主要指挥员,提高作战指挥能力。苏联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扩大边界冲突,频繁进行武装挑衅。8月13日,苏军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突袭中国边防巡逻队,打死28人。苏联强硬派还扬言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甚至就此征询美国的意见和试探东欧诸国的态度。
中苏边境爆发激烈冲突后,美国高层注意到苏联的强势,开始担心苏联“整垮”了中国,美苏之间的战略均势会随之被打破,而且美国对苏联乘自己陷于越战泥淖之机,大肆推行南下战略,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扩张势力范围,早已如芒在背,它有了实施“联华抗苏”战略的强烈愿望。但在珍宝岛事件期间,美国在公开场合仍然坚持既有的对华敌视态度,总统尼克松宣布,决定投入六七十亿美元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威胁”,并说“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中国共产党潜在的威胁之下”。国防部长莱德尔在国会作证时则明确说,中国仍然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潜在威胁”。给世界的印象是,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而对苏联则继续致力于维持战略均衡。
面对美、苏叠加的军事压力,我国进一步绷紧了战备弦。在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政治报告中提出:“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过去讲过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问了:他不来怎么办?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12]此后,“要准备打仗”成为指导备战全局的重要方针。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主要是针对美国的,那么1969年提出的“要准备打仗”方针,则是既防美也防苏,把美、苏视为同等敌人。
在“要准备打仗”方针牵引下,军队乃至整个国家迅速进入临战准备状态。(1)加快推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三北”防护工程,到1970年底在一些防御要点基本形成了依托山势的永备工事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掩蔽部、堑壕、交通壕相贯通的防御体系,可以储备粮、水、弹药以及屯兵,守备部队依托这些工事可以长期坚守、独立作战,迟滞敌军进攻,为国家转入战时状态争取时间。(2)全面展开战备交通、战备通信、后勤战备、人民防空等战备工程建设。从1969年到70年代中期,在“大三线”地区基本建成了由成昆、焦枝、湘黔、襄渝、枝柳等铁路构成的铁路网,在三北地区的主要战役方向建成了数千公里的、把前线与后方基地连接起来的公路网,长江、黄河的交通和航运条件得到改善;国防通信网建设成绩显著,基本上形成了由地下通信枢纽、长途地下电缆、微波通信网、架空明线构成的,以指挥所为中心的通信网络;后方基地仓库面积迅速扩大,作战物资储备充足,前沿阵地的弹药储备大幅度增加;各大中城市开展群众性修筑防空洞活动,制订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和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建立群众性消防、抢修、救护、治安等专业队伍,组织群众开展防空演习等。(3)扩大民兵武装。毛泽东在听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情况汇报时指示:“地方武装要像割韭菜一样。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三个营,可以不断地生长力量,生长主力部队。”[13]军委办事组座谈会据此部署民兵建设,要求全国各县建立民兵营、团,一旦打起来,能够建立地方武装,并补充野战军。至1972年全国组建民兵独立团1671个,独立连51330个,共计943万余人。(4)大规模扩编部队。继连年扩军,1969年军队扩编达到一个高潮,陆军增加了3个军部,组建28个师,改建2个师;空军组建了2个军部,组建8个飞行师,2个高炮师;到年底,军队员额达到631万余人,超过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军队员额(627万余人)。
此时,我国悄然开始调整军事战略方针。据熊向晖回忆,中共九大后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要求他们对世界大势进行研判,提出书面报告。1969年7月11日,四位元帅向周恩来送交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提出了与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当时国内舆论不尽相同的看法: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扩张实际上是在挤美国的地盘,美苏矛盾更经常、更尖锐,这样一种大三角关系构成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它们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也都知道中国不好对付,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是别有目的,是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苏联对我国的威胁比美国大,它在中苏边境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并在国际上大造反华舆论,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它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9月17日,四位元帅送交第二份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深入分析了苏联对华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认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作了相应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感到没有把握;苏联对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但美国绝不愿意苏联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一个资源、人力超过自己的大帝国,美国的这种态度是苏联发动对华战争的最大顾虑。送交这份报告后,陈毅又向周恩来作了一次口头报告,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如主动提出举行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14]。
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看到四位元帅的意见后有什么表示,作为参与者的熊向晖也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及毛泽东对此有何说法,但毛泽东此时显然也在考虑如何运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拓展战略回旋空间,毕竟同时应付两个强敌、进行两线作战是战略之大忌。1969年1月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表示中国注意到这篇演说中所表达的对华政策新动向。12月间,毛泽东看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关于美国驻波兰大使表示尼克松本人愿意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会谈”的报告后说:“找到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15]随即毛泽东批准恢复已中断了3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明确说道:“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6]向美国释放出愿意进行首脑对话的信号。1971年4月,毛泽东批准参加世界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随后,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愿意接待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国务卿、甚至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商谈。尼克松很快传来口信,表示接受邀请。7月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敲定了美国总统访华行程,并以双方公报形式宣布了这一消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尼克松,对他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17]这表明,中国不再把美国视为现实的战争威胁,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毛泽东于1月间在和周恩来等人谈如何答复美方口信时说: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18]。这番话道出了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意图。
中美共同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使我国安全态势有了重大改变,扭转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拓展了国际战略空间。据此,我国军事战略方针也随之有了调整。首先,军事战略重心转到“三北”方向。如果说1969年讲“要准备打仗”是准备同时应付美、苏两家,而这时讲“要准备打仗”则是只准备应付苏联一家。从这个时期军事建设和战争准备实践看,战场建设、装备研发、部队训练、物资储备等都瞄准对苏军作战,突出提高“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能力,特别是着重提高有核背景下的打击坦克集群的能力。其次,初步修正大战已经迫近的判断。虽然这个时期没有放弃“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但是已不再认为大战迫在眉睫。7月24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谈国际问题,曾说道: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19]。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也多次讲道:从现在看来,战争可能推迟一点,我们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把苏修孤立起来了。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指出: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战争在三五年内打不起来,有可能推迟,我们必须争取可能的时间,搞好工作,准备打仗。据此,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决定用3年时间减少军队员额160万。这个举动表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回顾20世纪60—70年代的军事战略方针调整,概括地说,进行了四个方面转变:一是由准备应付局部战争转变为准备应付有核背景的全面战争;二是由准备应付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转变为准备应付美、苏合伙入侵,再转变为准备应付苏联入侵;三是由准备阻敌于边境或沿海地区转变为诱敌深入,扩大了组织和实施反侵略战争的战略纵深;四是由经常的战争准备转入临战准备。总结这个时期贯彻和落实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实践,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把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概括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八个字,仍然把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作为战略着力点。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虽然美、苏争霸仍在继续,但世界缓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安全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战争的威胁感显著减轻。国内政治气氛因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有了根本转变,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军高级将领开启了对军事战略方针的新探讨。
1979年1月,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粟裕在军事学院对高级系毕业班谈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问题,提出在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首要问题,就是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从被动中夺取主动。这就要求,既要避免和敌重兵集团进行决战,又要通过积极的作战行动,迟滞敌人的进攻,以达到保持战争的能力,实现战略展开,调整和加强防御体系,从而顿挫敌速战速决企图,使战争初期出现相持局面。据此,战争初期可考虑主要采取依托阵地和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辅之以敌后游击战和游击性的小规模运动战来实现积极防御。粟裕的这个讲话在全军引起一场大讨论,使人们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方法的思考开始摆脱把诱敌深入教条化、绝对化的禁锢。
1980年9月,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向中央军委呈送《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直言不宜将“诱敌深入”和“积极防御”相并列作为统管全局的战略方针,因为积极防御是贯彻战争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战略指导原则,是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以及全国各个战场都必须贯彻的,而诱敌深入则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局的战略指导原则,不仅战略反攻阶段不适用,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也是有守有攻,攻防结合,不能都搞诱敌深入,实行全面退却。同时,我国边境地区大多有山地,是我军作战的有利条件,不能轻易放弃,而且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成果是打赢反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也绝不能让敌人白白拿去或破坏掉。更重要的是战争样式已经有很大变化,二战后发生的局部战争大多是局部肢解、代理人战争或抓一把就走,如果我国还实行诱敌深入,正中敌人下怀,要吃大亏。因此,建议我国军事战略方针还应该是1956年提出的“积极防御”四个字。这个建议得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的支持。
粟裕、宋时轮等高级将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应实行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方针所进行的探讨,对于纠正20世纪60—70年代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产生的偏差,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军事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80年10月,总参谋部举办防卫作战研究班,邓小平于15日到研究班讲话,他说:“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20]从此,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八个字改回到“积极防御”四个字,这绝不仅仅是字面的修改,而是增强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普遍指导性,有利于正确发挥军事战略方针对军事建设和战争准备的统领功能,并为依据国际形势发展和国家安全需求变化调整军事战略方针、探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创造了空间。
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正式宣布:“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21]根据对战和大势的这一新判断,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决定军队建设由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这实际上是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彻底放弃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方针。但这又不是一次完整的调整,因为这次调整军事战略方针的完整内涵应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放弃临战准备方针,要求充分利用大战较长时间打不起来的有利条件,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全面建设,为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做好经常的、长期的准备。二是放弃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移到准备应付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上来。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紧迫要求,是结束国家军事建设的临战准备状态,以确保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因此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首先解决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只解决了放弃原方针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移的问题。198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明确规定军事斗争准备由主要立足于应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主要立足于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至此,我国完成了新一轮军事战略方针调整,20世纪60—70年代所制定和执行的军事战略方针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国的军事建设和战争准备迈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如何评价20世纪60—70年代的军事战略方针调整,是研究新中国史不能回避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国家安全形势作出如此严峻的判断,首先是对国际政治、军事压力加大的必然反应,同时也和党的指导思想偏“左”不无关系。再有,战略后方建设过急过快,过于强调“山、散、洞”,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但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此次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敌视我国,从南北两个方向施加军事压力,我国所面临的战争危险陡然增长。防备战争风险的安全系数必须有裕度,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这是一般常识。毛泽东当时反复强调: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不做准备,敌人就来了。这就是战争准备的辩证法。如果当时不做大规模战备准备,很难说美、苏会不会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国头上。更何况我国通过大规模战略后方建设,在完善国家防御体系的同时,调整了国家工业布局,改善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建设条件,为今天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绝不能因为某些偏差,而全盘否定20世纪60—70年代的军事战略方针调整。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从历史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注释:
[1][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第434页,第520页。
[3][4][6][9][10][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第220页,第229页,第276页,第316页,第35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页。
[8][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1—842页,第849—85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14]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206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7—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6页。
[16][17]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页,第595页。
[18][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第441页。
[20][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第273页。■
(责任编辑 陈晓红)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