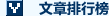苦难出诗 战乱励志——日军大轰炸下的山城重庆
杨耀健
导语: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国土沦丧,国民政府11月迁都重庆,使之成为战时中国首都。在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的三角地带内,集中了上百万人口、上千家内迁厂矿,其中包括十多家兵工厂,乃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命脉所系。正因为如此,日军将重庆列为重点轰炸目标,对其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企图摧毁和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决心。面对日军轰炸,重庆军民向死而生,顽强抵抗,共御外辱,保家卫国。
黑云压城城欲摧
1938年2月,日机首次偷袭重庆市郊的广阳坝机场,拉开了大轰炸的序幕。同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将汉口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成能容纳几百架飞机的军用机场,另外赶修运城、彰德等机场,用于轰炸重庆。初期配置两个陆军飞行战队、两个海军联合航空队、两个航空兵飞行团,各类型飞机共350架,此后数量逐年增加。
日军出动的机群为数十架,最多时出动近200架,携带炸弹、燃烧弹。从武汉到重庆,空中直线距离1000公里,单程飞行约3个小时,空袭时间多为晴天或月夜。轰炸重点早期为军政机关,之后变成无差别轰炸。
当时重庆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一旦被炸就会燃烧。不少市民没有防空经验,听见紧急警报,有的人还忙着收拾家中财物,有的人只是钻到八仙桌下,以为就可避炸弹,因此市民死伤惨重。
1939年日机以中央公园为地面坐标,分区投弹,造成的破坏最大。从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重庆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了一片火海,l9条主要街道变成废墟。城中心的鸡街、柴家巷被炸平,左营街、绣壁街、段牌坊、储奇门、玉带街等被炸得难以辨认。
日军还公然违反国际公法,肆无忌惮地轰炸各国驻重庆机构。英国、法国、苏联大使馆以及基督教青年会、英年会、法国圣心堂、苏格兰圣经会中弹。德国海通社、法国法新社、苏联塔斯社等外国新闻机构亦遭祸殃。尚未与日本宣战的美国军舰“图图拉”号中弹搁浅。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报道:“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在一两个钟头内延展成许多火堆,永远吞没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后街、小巷,以及转弯抹角的殿堂里,数千男女被烤死,没有办法救。”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大部分是由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前所未见。”
1940年,日军执行《101号作战》,预定轰炸重庆3个月,组成联合空袭部队,配置新式中型轰炸机数十架。轰炸重心转为“市区周围潜在的战略、政略设施”,及市郊的工厂、学校、机关。在第一波连续4天的轰炸中,日机投弹812枚,炸死534人,炸伤900多人。裕丰纱厂、军政部纺织厂等被炸。复旦中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南开中学中弹起火。始建于北宋年间的长安寺,有着近千年的历史,是城内的大庙,也被日军燃烧弹命中,只剩一座侧门。
1941年,日军采用所谓“疲劳轰炸”的战术,从有规律的集群轰炸改为无规律的间隔轰炸,即不分白天黑夜轮番来袭,使得市面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轮渡停航,人们仅靠自备干粮度日。
“疲劳轰炸”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一次死亡2000余人,不得不出动军警协助处理。参与掩埋遇难者的民工曹德全回忆:“一车又一车死尸拉到江北黑石子,最先一人一具薄棺材,很快用完棺材,直接入土。我一天负责掩埋五六个人,刨坑在内,长官还嫌我手脚慢,吵我。”
大轰炸下的市民生活
发电厂时常被炸,电动警报器往往不能正常使用,重庆防空司令部根据山城特点,因地制宜,在市内制高点悬挂球形灯笼报警。灯笼大约2米高,圆形,内装煤油,分红、绿两种。敌机经过万县(今万州)时发布预警警报,悬挂1只红球;敌机到涪陵,悬挂两只红球;敌机即将飞临,悬挂3只红球,为紧急警报;悬挂绿球,则表示敌机离去,空袭结束。重庆城内至今还有“红球坝”这一地名,可谓历史见证。一见红球高悬,市民便赶紧奔向最近的防空洞,称“跑警报”。
抗战初期,重庆便不断开凿防空洞,共挖掘防空洞数百个。这些防空洞依据山势,横向开凿2米宽3米高的巷道式洞穴,进深十余丈,一般可容百人,无须水泥坑木加固。只是战时物力艰难,防空洞通风设施简陋,照明使用蜡烛或煤油灯,空气浑浊,人多就觉得喘不过气来。
市民吴伯荣回忆:“小洞无凳,找到一块石头或半块砖头就地坐下,已可满足。人们不可能站立几个小时,何况站着影响空气流通,也是不行的。阅读不可能,除聊天外就只有打瞌睡。几个钟头呆在洞里,又渴又饿,还不能及时上厕所,十分难受。”
市民顾大纲回忆道:“我第一次钻进十八梯的洞子,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了人。防护团员拉着我向里边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那滋味可想而知。一小时后出洞,阳光刺目,好一阵才适应。”
战时重庆市民恪守社会公德,跑警报时有的商店、副食品店来不及关门,但从未发生过盗窃或抢劫事件。有时餐馆里宾客满座,忽传警报,众食客赶忙散去,然而之后都会回餐馆结账付钱。市民陈未云一次在街头理发,刚剪了半边头,警报大作,他顶着“阴阳头”和理发师各奔东西。警报解除后他找到理发师,见对方平安无事,相视一笑,接着理发。
当年还是小学生的市民齐仕蓉在回忆录中记述:“为了躲飞机,家里数次搬迁,我也多次转学,有时在鹅公岩,有时在化龙桥,有时在江北,有时在沙坪坝,有时上正规学校,有时上私塾或在家自学。上课时常常拉响警报,背上书包便去找防空洞,警报一解除,又回教室上课。晚上睡梦正酣,被刺耳的警报声惊醒,只得从热被窝爬起来,跟大人一道去附近的山洞或挖空的墓穴躲,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去找大一点的防空洞藏身。”
房屋被炸而无家可归者,食宿均成大问题。重庆1939年设立振济委员会,在空袭期间开设茶粥站,解决灾胞饥渴。在千厮门及南岸搭建席棚,临时收容难民。粥厂先是免费供应两餐,米饭、稀粥各一顿,后因经费短缺,改为平价出售粥饭。
孤儿刘祥云回忆,父母及姊妹5人死于空袭,他沦为乞丐,靠粥厂救济维生,后来被送到制革厂做工人,得以存活。他回忆说,前往就餐者均为灾民,未受灾者绝不去冒领,就餐者排成长队,依次序领餐或购买平价食物,给疏散人口发疏散费,直接交给灾民本人。
山城各界齐抗争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奉命拱卫重庆。印尼华侨飞行员梁添成在“五四”“五一二”“五二五”空战中,总是升空迎战,每次都有一架半架(与战友合作)的战果。每当从天空看见山城浓烟滚滚,他都咬牙切齿地发誓说:“狗东西,如果我下次不打它两架下来,我也不回来了!”因战果累累,他被誉为空军“四大天王”之一。1939年6月11日黄昏,又有20架敌机来袭。这一天并不该梁添成值班,可他听到敌机来袭的消息就跳了起来,跑到飞机边跨进座舱。梁添成升空后发现了敌机,追上去不停射击,击中一架敌机后,自己的座机也中弹坠落。
空袭时,交通警察负责疏散车辆。警士吴国强早上离家时,妻子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做早餐。吴国强的岗位在通衢大道临江门,是主干道。他刚接班不久,敌机临空投弹,他手持指挥棒,疏散车辆。一枚炸弹在岗亭附近爆炸,吴国强倒在血泊中。妻子闻讯赶来,只见他挎包中还有一个来不及吃的烧饼,失声痛哭。
警报解除后,消防队立即出动,哪里火势大就先去哪里。消防设备落后,起初只有六七辆消防车,顾此失彼。而在轰炸中自来水管多被炸断,救火主要依靠人力。一台人工泵由两位消防员分掌左右,他们紧抓手柄,前弓后蹬,用力压动水泵,向火场喷水。其他队员则用简陋的工具开辟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消防队中队长王开元、分队长徐敬,在第一批敌机轰炸后率领队员救火,不幸被接踵而至的第二批敌机杀害。大轰炸期间,80余名消防官兵以身殉职。《新华日报》刊登消防队员来信:“我们的水龙那样少,我们救火的设备那样贫弱,然而我们有的是伟大的人力。多少人忘记了生命危险,在火舌上窜来窜去,我们即使不能立时扑灭火源,却一定要阻止它的燎原。”
空袭服务队负责救死扶伤,空袭后他们冒着浓烟烈火,踏着灼热的瓦砾,穿行于断壁残垣中,救助被困市民。他们用锄头、铁铲刨去地面重物,接近被掩埋者时,就用手去抠砖石,以免伤到幸存者。对轻伤者进行包扎,重伤者则用担架送到附近的医院。一日夜里,空袭服务队的刘安民在南纪门附近的废墟搜救,从倒塌的油蜡铺下挖出一对母子,已过大半夜,正想休息一会儿,耳边传来微弱的呼救声。他循声而去,发现呼救来自垮塌的梁柱之下,他赶紧搬去一些重物,这时呼救声突然中断,他加快行动,终于又救出了一位幸存者。总队表彰他时,他却说:“我不配,我不配。那次在新丰街,有两个人我没有来得及施救,挖出来都已经停止呼吸了。”
慈云寺成立了“重庆市僧侣救护队”,由觉通和尚担任队长,参加过淞沪抗战的乐观法师也加入了救护队。青壮僧人穿着圆领短装,佩戴红色“佛”字袖章,参与救死扶伤,备受社会好评。僧人释世诚在抢救伤员时中暑,救治无效辞世。
结成砥柱御狂澜
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各院部奉命疏散郊区,市区留有主管及重要人员处理紧急公务,重要事项备文呈报中央党部、行政院及军委会。日本电台称蒋介石已去成都,国民党中央即将迁离。其实,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一直留驻重庆。1941年8月,日机突袭蒋介石官邸,宣称蒋介石已被炸死,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随即报道蒋介石出席“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戳穿了日本电台的谎言。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工作人员迁往红岩村。周恩来、博古、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常住城内曾家岩50号。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人,都在重庆。
大轰炸期间,兵工厂一直坚持生产。第21兵工厂被炸14次,月产上万支枪械,可武装一个师。第50兵工厂70多名员工伤亡,月产37毫米战车防御炮5门、60毫米迫击炮100门。第25兵工厂员工伤亡130余人,月产子弹数十万发。第10兵工厂伤亡40余人,年产迫击榴弹、曳光弹、迫击炮弹数十万发。重庆各兵工厂生产的火炮、枪弹,大量杀伤日军。
第21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年逾五旬,事必躬亲。他住在办公室,隔壁厂办的三部电话机铃声此起彼伏,他必要去旁听,遇有情况及时回复。白天他在厂里巡视,晚上仍在办公,有时累得不行,只能躬身行走。第50兵工厂老工人赵国玺回忆说:“名为三班倒,其实加班加点是常事,经常要连上两班。工人们知道是为了保家卫国,从无怨言。”第24兵工厂技师朱继林说:“轰炸不仅不能阻止我们,反而促使大家抓紧时间。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365天,敌机上午来轰炸,我们下午做;下午有轰炸,晚上做。今天不能上班,明天加班做。”
电力是城市的动脉,电力工人全力地维护着。空袭一过,马路上立即发现许多身上背着沉重的电线和工作用具的电厂工人,猿猴般爬到电杆巅上工作。有时空袭警报已经拉过,路人都跑入防空洞去,我们无名的电力英雄们依然在那里接线。
中央大学中弹上百枚,实验室、大礼堂、宿舍被炸毁,员工伤亡10余人。校长罗家伦说:“最近两次被炸,损失颇大,但被炸者系物质,不能炸毁学校的精神。”全校师生在暑假期间加紧抢修校舍,使中央大学成为沙坪坝区最早开学的大学。南开中学1939年运动会原定5月举行,但当时日机轰炸频繁,经校务会议讨论,运动会如期举行。校长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陈词:“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们的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去做。我们要干到底,顶到底!”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等50多个文艺团体,活跃在宣传第一线。话剧界连续四年举行“雾季公演”,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四次被炸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向观众贡献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民族万岁》和数十集纪录片。
不屈不挠的山城
从l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炸死炸伤市民近3万人,毁损房屋3万余栋,其他财产损毁更是不计其数。斯时,重庆市政府要求市民在家门口悬挂一盏灯,方便夜间疏散。千家万户都挂出白纸糊成的灯笼,不少灯笼上写着:“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
重庆未曾屈服。汪精卫叛逃,全民声讨。日本诱降,断然拒绝。围困封锁,自力更生。“愈炸愈强”的标语,体现了重庆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理发店里贴着一副对联:倭寇不除,有何面目?国仇未灭,负此头颅。饭馆里的锅巴肉片,取名“轰炸东京”,夹沙肉取名“踏平三岛”。饭馆墙上的联语为:复仇雪恨每饭不忘;杀贼驱倭投箸而起。
德国友人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中国人民过去曾备尝痛苦且于忍耐力持久力方面,更具悠久传统,绝不因任何形式之胁迫而放弃其抗战建国之目的。目前全世界任何地域,对于最后胜利信念之坚,恐无出中国之右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参与重庆大轰炸行动的敌人,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指挥“101号作战”的海军将领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在太平洋战争中先后切腹自杀。在汉口基地发号施令的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二战结束时被判终身监禁。执行“五三”“五四”大轰炸的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驾机指挥突袭黄山官邸的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在“南方作战”中下落不明。■
(作者单位:重庆市文史研究会)
(责任编辑 王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邓园”往事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