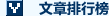民国报人俞颂华:风雨浮沉 风骨铮铮
周利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人俞颂华蜚声中国新闻界。近些年,对他的研究文字较多,但对他的生活和病因却少有人提及。笔者查阅了1947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人物杂志》《国讯》《大公报》《申报》等报刊,从其家人、友人、同事、学生的追思文章中,看到一个为了生活颠沛流离、为了信念屡遭排挤、为了事业殚精竭虑的民国进步报人。
一代报人 进步人士
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中学、复旦公学,从小立志做一名利国利民的记者。1915年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回国后,1919年初,曾赴海参崴担任日文秘书,终因旨趣不合,不辞而别。同年4月任职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宣传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陆续刊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全文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1920年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身份赴苏俄采访,同行的还有瞿秋白与李仲武。俞颂华是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苏俄状况的中国新闻记者。他采访了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撰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报道,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又改任两报驻德国特派记者,1924年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1932年5月,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邀主编《申报月刊》(后改周刊),这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最佳时期。他特邀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人士撰文,讴歌正义和光明,鞭挞反动与黑暗。《申报周刊》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最大的刊物。1937年4月,他赴陕北采访,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撰写了《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成为‘国难中的一线曙光’”。他在陕北还拍摄了大量照片,分期在《申报周刊》上刊登。他敢闯禁区,敢讲真话,在国民党统治下是极其了不起的,也是继斯诺、范长江之后客观报道陕北实况的又一名进步记者。
抗战爆发后,《申报周刊》的停办成为俞颂华一生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40年夏,他离开重庆去香港,在香港先任《星报》总主编,由于与同仁志趣不同,数月后赴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9个月后,因国民政府要控制海外华侨舆论,他被排挤回香港。1941年10月,应梁漱溟之邀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转移到桂林,任《广西日报》主笔。1943年5月,应《大刚报》社长毛健吾之邀,赴衡阳任该报总编辑。1944年4月,《大刚报》馆迁往贵阳,俞颂华经不住长期颠沛流离,身体虚弱不堪,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又抱病任《国讯》半月刊主编。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回南京,特邀请他仍旧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控制时,便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过着清苦的生活。同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他应邀任该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夏秋以后,他肺病加重,卧榻不起,10月11日在拙政园病故,时年54岁。
“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是公正精神,不为偏见所蔽;为文论政,要大公无私,代表人民;要忠于职守,淡泊名利”,这是俞颂华对一名优秀报人应具备素质的论述。
俞颂华的女婿葛思恩在《悼先岳俞颂华先生》一文中介绍说,俞颂华先生一生生活淡泊,不计名利,立志坚定,嫉恶如仇,时常提起的两句口头禅是“知足常乐”“无欲则刚”。他立志不进仕途,不入任何党派。在《东方杂志》任职期间,主编钱智修等曾力荐他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当即遭到他的拒绝,甚至对于进入仕途的朋友,也有意疏远。他于1940年夏离开重庆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陈立夫要他加入国民党,他拒绝后便远去香港。此后,虽然在香港为梁漱溟编过《光明报》,在重庆为黄炎培等办过《国讯》,但并未加入民盟或“职教社派”。抗战胜利后,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曾邀他赴北平办报,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加入该党,俞颂华坚守信念,仍旧未允。
《大刚报》编辑严淮冰在《一代报人 寂寞长逝—俞颂华先生的生平》一文中写到,俞颂华一直就是一个职业记者,靠应得的收入养家糊口,在这一点上,与名报人张季鸾不同:张季鸾是《大公报》的老板,有事业在手,意志比较自由,生活上不受任何威胁;而俞颂华一向做伙计,虽然有意志的自由,但只有在报社老板与他的意见相接近的前提下,始能合作下去。所以,俞颂华30年来,是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情形下由这家报馆到那家报馆,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信念,甘愿受尽生活上的磨难。
俞颂华有两句座右铭:“欲除烦恼须忘我”“各有因缘莫羡人”。晚年的他两袖清风,一身是病,以“忘我”的精神,忘掉身体上的痛苦,拼命工作。
生活清贫 平易近人
俞颂华的太太在上海某银行做事,儿子俞彪文在上海中央信托局工作,女儿俞湘文在常熟教书,女婿葛思恩是政治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与俞颂华衣钵相承。按常理讲,这个家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小康之家,但因俞颂华体弱多病,全家收入的大半都用于为他诊病吃药上,所以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重庆时,俞颂华的背已经弯成45度,但为了生活,还得工作下去。担任《国讯》的主编时,因收入微薄,他只得参加集团的大伙食,饭菜令人难以下咽,但他却不以为苦。他夫人为增加收入、能给他加点营养,后来不得不出去工作,他的儿子白天做事,下班后读夜大,自食其力。在这种艰苦的情形下,每当别人问及他的经济情况,他总是怒目以视,不要身边的人谈及此事,他说:“我是可以活下去的!”葛思恩回忆说,1946年冬天,俞颂华的大衣破烂不堪而无力添置,幸而后来俞庆棠女士赠他一袭,才得勉强过冬。然而,在《申报月刊》《申报周刊》时代,凡举行座谈会、招待会,他都是自掏腰包,不开公账。
俞颂华对于自己的生活标准要求不高,但对待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上至为关切。大概一个失去健康的人更知健康的宝贵,他总是对学生多方照顾,以免他们重蹈自己的覆辙。严淮冰回忆说:“为了让我少吃酒,他曾当面使我的一些酒友难看。为了使我有足够的睡眠,更是一早就坐在房门口,不论任何人,一概不准来打扰我。关于我与严问天兄的婚姻问题,他老人家也常常操心。记得我与妻刚认识的时候,俞先生就担任我的恋爱顾问。每天晚上归来,他总要垂询一番,并且告诉我第二天的步骤。我本是情场的失败者,果然,这次在俞先生的指导下,我圆满地完成了婚事。当我与问天兄在筑举行联合婚礼时,俞先生在渝全家聚餐,为我们遥祝。”
友人谢在田在《哭俞颂华先生》一文中记述到,学生来访时,俞先生总是一脸笑容地热情招待,先送过来一支烟,再用顶好的茶叶沏上水。他很健谈,学生说的时候少,听的时候多。他说罢一段落,就笑着问,你看我说的对不对?问过了又笑。谈得高兴,上午谈过,下午再来。谈话中小半是时局,大半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有时也谈他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不知疲倦。关于时局,他总是叹息,因为现实生活多是事与愿违。到后来,他说得越来越少了,终至三缄其口。他劝学生们多研究,少发表意见,总要学生“把握时间,努力读书”。对于学潮后离院的学生,嘱咐他们不要进报馆,最好去教书。他认为,在当年的形势下已经无报可办,清一色的论调,进了报馆势必要做违心之论,不如教书自修为好。
香港沦陷后,撤退下来的文化人,多集中在桂林,因此那里被称为“文化城”。这期间,俞颂华拖着病体,夜晚忙于《广西日报》的编辑工作,白天还要去科学书店策划该店的出版工作。他常说,报人是直接对读者负责的,所以,他不愿放弃任何可为读者服务的机会。正像严淮冰所评价的:“陶行知先生是由大学办到小学,越办兴致越高;俞颂华先生是由大报办到小报,越办越有劲。”
在衡阳主编《大刚报》时,是俞颂华相对安逸的一段时间。他的月薪2000元,是社长的五倍,同事们都对他很敬重,很少让他上夜班,但他仍住在报社,卧室就在编辑室的隔壁,半夜醒来常跑到编辑部帮忙,大家总设法让他安心,要他提早回去睡觉。尽管在这段时间,俞颂华的病症没有加重,但由于没有及时医治和疗养,也未见好转。晚间,他躺在床上,每一翻身,因腰酸背痛,情不自禁的惨叫声异常痛苦,就像囚犯受刑一般。听到这种声音,同事们都觉得,活着对于他来讲,实在是一件苦事。
因为身体原因,晚年的俞颂华在苏州改任新闻教育事业,但仍念念不忘办报。他常与人说,等我身体恢复后,还要回到南洋去办报,可惜他的厚望终未实现,饮恨而终。
积劳成疾 忧愤而逝
1918年留学回国后,俞颂华曾患过一场大病,医生建议将他的右手开刀,他坚持不答应,并说,日后写字的工作,将全靠右手。
抗战爆发后,俞颂华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到了香港后,俞颂华的工作吃重,精神压力大,俞夫人又不在身边,在生活上缺乏照料。他自己也认为,身体的坏就是从那时造成的。香港逃难,黔桂流亡,及至重庆与夫人见面时,虽欲就身体状况作根本挽救,但为时已晚,以致刚过50岁,他便已是老态龙钟了:背弯了,耳聋了,眼花了,牙也掉光了。可是为了生存,他不但得不到休养,还要拖着百病身体,竭其最后的生命力,继续工作。
直至抗战胜利后,俞颂华认为,精神上不再遭受恐惧,物质上不虞匮乏,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当陈礼江请他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开办新闻系时,他很高兴地答应下来,并计划用四年的时间,一面养病,一面训练干部,身体恢复后,他便可以带着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青年,一同赴南洋开发这块文化的处女地,创办一份像样的报纸。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位于苏州拙政园内,俞颂华住在园内的教职员宿舍内。清水、池塘、杨柳、荷花,环境很好,但糟糕的国事却让他的心绪无法好起来。战乱频仍、物价飞涨的残酷现实击碎了他的美梦。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地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学院学生积极响应,他也为学生捐款。但院方听命于国民党当局,勒令30名学生退学,眼见新闻系的学生默默地离院,他受到很大刺激,肺病随之加重,竟然吐血。更使他难过的是,学院新闻系不能完全贯彻自己的计划,他要聘请的刘尊棋教授,院方未能通过,而学校聘请的教授,学生又不欢迎。心灰意冷的他绝望地说:“我的事业计划只有老虎(俞颂华儿子的乳名)来完成了!”言罢,老泪纵横。
署名明心的作者在《俞颂华先生逝世前的情况》一文中记述了俞颂华的最后时刻。双十节的前一天,他从上海赶到苏州看望俞先生。在教职员宿舍里,他看见俞颂华一个人孤寂地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一个临时雇用的老妈子。他的太太和孩子都在上海工作,不能常来看他。他瘦弱得很厉害,吃粥需要人喂,小便也要人把便壶拿到床上,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支撑着坐起来。听说校医每天过来给他打针,明心就劝他应该住进医院,一切医疗护侍可以方便些。俞先生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住医院就得预缴保证金一百万元(实际上这个数目是公家医院最少的了),像我这样的穷苦公教人员,又哪里来这许多钱请特别看护呢?所以,只有请校医给我诊疗了。明心听后,心中一阵酸楚。病榻上的俞颂华仍关心上海方面一些朋友们的近况和有关文化出版的情形,言谈之间,他总是喟叹:“民生太苦,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他感慨时艰,关心世变,但身处病榻,无能为力,惟剩叹息了。看到俞颂华的身体这样糟糕,明心沉默着不敢多言,只是安慰他好好地静养,早复健康。但心中却想,这样的养法,怎么能够早日康复呢?
两天后,明心又约了朋友搭早车一同到苏州探望俞颂华。在列车上,他买了一份《大公报》翻开阅读,竟然看到“国际问题专家、现任国立社教学院新闻系主任俞颂华,因平时积劳过度,患病多年,卒于11日晨10时零8分病故”的消息。
俞颂华病逝后,遗体厝于昌善局殡仪馆,1947年10月12日下午4时举行大殓。11月2日上午10时,在苏州东北街上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大礼堂,俞颂华追悼会隆重举行。除该校全体师生参加外,各界代表及俞先生生前友好近千人前来致奠。为纪念俞颂华从事新闻事业30年,其生前友好出资设立“俞颂华新闻奖学金”。追悼会后,将其遗体葬于苏州城胜地灵岩山上,以便他人览胜凭吊。
1947年11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商务印书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东方杂志》等单位,江问渔、王芸生、张东荪、潘光旦、周诒春、叶圣陶、朱经晨、章乃器等90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俞颂华追悼会委员会,12月1日下午2时,在静安寺隆重举行追悼会。
《大公报》《申报》《国讯》等报刊纷纷刊登消息和追思文章。1947年12月15日《人物杂志》专门制作“颂华先生逝世纪念特辑”。
陈礼仁在《悼俞颂华先生》一文中写到,8月以后,俞先生几度吐血,于呻吟床褥之际,犹急急地物色优良教授,拟订教学计划,其忠于职守之精神,诚可谓鞠躬尽瘁。俞先生口德刚正而遇人和淑,视学生如子侄,爱之以至诚。因此,先生去逝学生痛哭失声,同仁无不暗自神伤,泪如雨坠。有一位学生写道:“我衷心地敬爱他,视他如父亲一般,我的悲痛亦不仅止于师生之情,我不但是为了个人失掉一位敬爱的良师,也不单是为了新闻系失掉了一位系主任而痛苦,更为了目前负他生前的教训和期望。”吕竹在《敬悼报人俞颂华先生》中写到,抗战胜利后,虽然俞先生一家均在工作,但工薪的收入远远不及飞腾的物价。俞先生月薪不足百万元,平素的诊病吃药皆由夫人省吃俭用地供给,“余惜俞氏早逝,报界无穷损失,社会无尽损失,而今日之社会有责任焉?”储裕生在《敬悼俞颂华》一文中拷问:“以他这样一个有学问又正直的人,社会上竟不能好好地保养他,让他受着凌霜傲雪的欺侮,这是谁的责任呢?”从中不难看到,众人无不痛斥国民政府,无不哀婉俞先生英年早逝,更可想见那一代文人之生存不易。■
(责任编辑 樊燕)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
- ·饶漱石的错误根源及其蔓延
- ·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 ·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
-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
- ·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
- ·杜聿明与大决战
- ·新保安战役:稍纵即逝的...
- ·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实
- ·义和团的兴起与失利
- ·心系天山未穷期(上)—...
- ·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
- ·冯友兰被捕背后的隐情
- ·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征战...
- ·“邓园”往事
- ·张勋的升迁途径
- ·耿飚将军与中巴友谊
- ·刘志丹在永宁山
-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 ·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